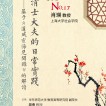9月22日上午10点,教育高等研究院引来了本学年的第一场学术沙龙,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肖瑛教授应邀而来,同大家探讨“公私之间——晚清士大夫的伦理实践”这一话题。此次沙龙由周勇教授主持,教育高等研究院和学部其他系所的十几位师生共同参加了本场沙龙。

在周勇教授的简短介绍后,沙龙随即开始。肖教授首先介绍他的问题意识:
我近年的个人学术兴趣主要在个人主义与公共性的关系上。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公共性的理解和个人主义存在误区,认为两者是对立的。我要厘清,个人主义和公共性是相互依存的,个人主义是公共性的必要条件,讨论两者之间的悖论性关系。先是对个人主义和公共性的内涵做了一个梳理,然后要回到中国,对中国现实的观察。这几年出现了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因为中国现状跟过去无法割裂,精神气质一直血脉相连,而回到历史不是抛弃当下,抛弃西方,社会学研究一直是在中西古今这几个象限之间。
核心论题:公共性源流家国关系公私关系
首先是公共性源流。我不是只讨论共同体,实际上共同体和个人主义之间存在张力,从古希腊一直到罗尔斯、桑德尔。古希腊是一种共同体,然后到洛克、霍布斯的个人主义,二战之后,阿伦特和桑德尔强调个人主义和社群的关系。其次是家国关系,这要涉及到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血缘关系的问题。我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梳理,《共和国》《法律篇》《尼各马可伦理学》到《旧约》《新约》,西方传统中如何理解血缘关系,然后跟《孟子》《论语》《礼记》《大学》进行比较。中国传统讲的是修身,这在理学当中表现非常明显。中国实际上是家国一体,古希腊,家和国是分离的。最后是公私关系,公私关系和家国理解是不一样的。带着这样的兴趣我回到了张集馨的文本(《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来。
张集馨生于1800年,于1879年去世,活了79岁,江苏仪征人,29岁就中了进士,在翰林院做了八年的工作。1836年做县知府,从此他先后在福建、陕西、四川、河南等地任职,还去过甘肃两次,担任了粮道、监察史、巡抚等多个职务。他遇到了很多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人,像林则徐。他一共四次被弹劾,第三次的主角是曾国藩。到1865年又被陕西巡抚弹劾了,从此他的官场就彻底没落了。
他的生命轨迹同天朝崩溃前期的动荡完全合拍的,他和林则徐、曾国藩等在天朝大员过从甚密,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看他的日记就可以看到清朝没落的历史。他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人,对于陋规他坦然接受,但他又竭力拉开与同僚的距离。他生性敏感、洞察力强并且笔法细腻,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他的日记不仅是洞察晚清官场生态的一个窗口,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儒家的官僚在道统与政统、家和国,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方面的挣扎和紧张感。他这个文本在历史学上是非常重要的,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另一本《潜规则》中运用比较多,但社会学基本没有关注的。我最近几年关注一些历史的小说、日记,包括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我们把它看做人类学中完整的资料来看,对文本背后的生态想象,从社会学角度来寻找问题并分析,《道咸宦海见闻录》也是这样。
公与私的思想简史
我简单介绍一下公和私关系的简史,我的分析基本是到1900年,主要是清末之前。按照沟口雄三的说法,它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封建时期,道统确立的时期。根据《公羊传》中的“公”和“私”,“公”是指公家、官家,实际上就是贵族、王侯,“私”主要是老百姓。到了春秋战国,“公”和“私”开始具有了抽象的价值义,“公”就是公正、公平、平均,是一个褒义词,“私”是一个贬义词,“公”和“私”的分化就很明显了。第二个阶段是宋明理学的阶段“存天理、灭人欲”,将“公”和“私”做了绝然的对立,公和私、利和义、少对多一一对应,“私”代表着特殊,代表着多,人欲是多样化的,当然私并不完全是错的和贬义的。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是“修身”的,沟口雄三说“私”是个人的欲望,“公”是士大夫内在的道德,他的“公”和社会是没有关系的。到了明末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明末工商业的发展,如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李贽等人,对“公”与“私”的理解发生了很重要的转变。宋明理学用定型的“理”观念来规范现实。明末时转变为,用现实来规范“理”。因此“公”成为了每个人都能从社会中各得其所这样一种公共法。此时“公”就是“私”——即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得到我们应当得到的那个“私”,“公”就建立起来了。沟口雄三说,中国的公私观还是在第一个阶段奠定的,即道家与儒家的观点,实际上构成了公私关联连带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天之公私”即日常所说的天道,具有终极性与普遍性。
——第二个层次,是君主、国家与官员之间的关系。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公”和“私”。
——第三个层次,“共同体”的公和私。比如中国传统大家庭。如果主张分家,便被视为“私”。
在封建时期,它们不会产生太大的紧张性。但是当郡县制建立,即秦朝专制体制建立之后,这种紧张性便会非常明显的呈现出来。最明显的紧张性是天的公私与君国官的公私紧张性,也就是道统与政统的关系。
从前面可以看出,道统在公私界定及其关系上的想象清楚且明细,三个层次非常清楚的,问题在于:
1、具体的伦理实践会如何,特别是从封建制进入郡县制后?从“公天下”进入到“家天下”之后,这种“公”和“私”,伦理与伦理的实践便产生了紧张。“公天下”与君、国、官之间的关系。
2、士大夫如何面对道统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再生产出新的现实的?应当忠实于公、天道?还是国家和君主?他们如何面对这种紧张,面对紧张时的实践又如何生产出现实。
3、其伦理实践的紧张和后果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分析第二、第三个问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这是我的文章的三个部分,现在从三个问题对章节性的文本进行解读。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家庭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利与私利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关于他身份的关系,也就是他作为士大夫和官僚本身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一、小家庭与大家族:苦难共同体及其超越
在社会学中,共同体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共同体最早是在德国社会学家暨哲学家滕尼斯的《共同体与公民社会》中提出。他认为,共同体与公民社会有些类似于哈贝马斯的生活实践与系统的关系。共同体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存在,是以血缘、地缘、信仰等勾连起来的。我们所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我们的来源,都源于共同体内在的共同文化和价值观念。“civil 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可能会更妥当,它来源于黑格尔的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后又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中提到,强调的是按照市场经济模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在市场生活中,一切人与一切人都是敌人,一定是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条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条件)和目的。所以,“community”和“civil society”的一种对立,“community”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civil society”是今日处在商海与城市森林间的生活,人们行色匆匆,面无表情,盯着自己的手机看。
“共同体”这个词被滕尼斯赋予了一种甜蜜的色彩,是我们安身立命、心灵停泊的港湾。然而现实的共同体却 “必须发挥组织劝诫与道德服从的作用,共同体必须是强制的和道德的。”在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即共同体与财产的分割是对立的。我们如果只言利,不言义,就会造成我们很难在共同体中实现自己的欲望,会受到镇压。因此共同体除了甜蜜,还有一份苦难。但没有苦难就没有甜蜜。我们每个人不能有过多的欲望;但也因此,共同体给我们守望相助的依靠。因而我把共同体称为苦难的共同体,也就是苦难和甜蜜的一种交织。这种共同体的前提是公私区分的模糊。
在中国的共同体意识上,儒家伦理是家庭至上的,例如论语中讲的“父子相隐”。孟子讲的“瞽瞍杀人”也说明“父子有亲”比“君臣有信”要重要得多。在《旧唐书》中讲了一个九世同堂(百忍堂)的故事,这就是中国对于大家庭的一个想象。
但是张集馨对于大家庭的记忆和想象却只有八个字——纠纷不断,人情冷暖:父亲和祖父的争吵,与伯父家的人命官司,亲戚欠债不还等等,张父去世后,张集馨要参加科举但无人关心他,无人知道他去京城应试,也无人送行。因此大家庭在张集馨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中间,只有那八个字。所以他想用分家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超越苦难共同体:分
有个官员被家里的亲戚嫌弃(穷),分家产时不分给他,因此闹了矛盾。张集馨就说:“余思家不分析,终是葛藤”,让五个人分了家。还有母子不相认,儿子不养母的案件,“遂令回州将产分派停妥,无许偏倚,写分书三分,当堂阄定”。
张集馨觉得“分”很好,而这恰恰与把大家庭看成“公”是对立的。但另一面,他没有将大家庭的冷暖抛之脑后,“每年周恤亲族,仍注存之”。他对家庭的态度是两重的:一是对大家族没什么好感,他要“分”。但分完之后,他认为大家庭的意义还存在,所以他会从儒家伦理的角度来对大家庭进行呵护。
大家庭等于“公”,小家庭等于“私”,在个人欲望不能消解,财产边界不清晰的情况下,形式上的大家族往往在各种纠纷中消解了被期待的“公”。“分”令财产变得更加明晰,人和人的活动空间上的边界越来越清楚,重叠性越来越小,反而可能为“公”创造条件。但是分本身不能带来公,所以儒家的家庭伦理就显得十分重要。所以他在朔平做知府的时候,将办学教育提到了重要的位置,来解决“关北人无伦理,父子夫妻,不翅路人”的问题。儒家伦理作为一种外在的意识形态,对于大家族的公的重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国利与私利的关系:卫国与徇情
1、断案中执法与人情的调和
张集馨对琦善的看法:“未尝不徇情,然必于理不悖,始肯顺手推舟…未尝不要钱,然必审度其人,实是可以造就,公事结实可靠,方肯收受…”琦善就是一个将私利与公利结合的比较好的一个人,这也是张集馨的自我写照。他处理朔平兵饷案(1836年)、哈楚暹京控满营案、犍为县令朱在东任上“亏短正杂款项九万余金”案的时候,都是让涉案官员退还自己所侵吞的财产,补上亏空,息事宁人,尽量减少各方损害。他自己说“公义私情,两多裨益”,另一个就是“余诸事平正”,这是“摆平理顺”的关系,既不是按照推理或证据的逻辑,也不是坚持正义,而是把损失弥补上,把关系处理好,每人都退一步,这种现象是非常多。应星专门讨论过中国的地方官员怎么用“摆平理顺”的手段处理社会各种关系。这是中国独特的现象,如朱苏立先生说的送法下乡,法律的本土化资源,就是一种摆平理顺的关系。还有部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也是讲摆平理顺的关系。表面上的平正造成帝国制度之“公”的暗地流失。因为官员还会再做类似的事情,张集馨也是保存自己的“私”,他要防止关系网络把他吞噬掉。
2、捐班背后家利与国利的紧张
捐班,即买官卖官,这是制度化的,皇帝都允许的,因为财政出现了问题。捐官是一种以利为利,将本求利的生意做法。而科举上来的人都接受过正规教育,礼义廉耻还是在的,虽然可能会贪污腐化,但一点拨可能会转过来,这是君子怀刑的传统。
张集馨认为捐班是一种坏行为,在日记中提到多种捐班行为并表达厌恶,然而他自己曾花钱为大兄、侄子和自己的独子兆兰捐班。从道光的言论看出,捐班从“公”的角度看是矛盾的。它可以缓解帝国财政困难,这样来看是“公”,然而捐班进入帝国的官僚体制内会导致贪污,对帝国不利。张集馨犬儒主义的做法,心理认为捐班损公,瞧不起,行为上他认为是在缓解帝国财政危机,不认为自己有损“公”。
3、陋规中的私利与国利
陋规是清朝官场上的规定性的动作。林则徐、琦善都受到陋规的影响。一个原因是低薪,雍正以前,官员薪水都很低;第二个原因是公私不分,外官赴任路费都自己出,而且收取的税费之类的,有点像承包制,除了交给国家的,其他的都由自己来支配。所有公共开支,都由自己来掏钱,能收多少钱,就可以用多少钱。整个财政公私不分。
美国教授曾小萍在《州县官的银两》讲到雍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财政理性化改革,就是公私之分:提高官员的薪水,让他们凭薪水就能过有体面的生活。他把锻造银子时的冶炼流失,即火耗,交给国家,由国家进行一种重新的分配。但乾隆取消了火耗归公的制度,陋规就重新回来了。结果就是,京官没有什么好处,只好从外官那里得好处。外官做粮道、盐道或地方官,有一堆老百姓可以供他盘剥,形成了非常恶劣的关系。
张集馨的陋规:他从京城到陕西去赴任时的“别敬”( 孝敬京官)是一万七千两。每年还有“炭敬”( 冬天买炭取暖的钱)和“冰敬”( 夏天买冰降温的钱)。他做粮道时,每年给京官的钱是五万两的样子,陋规非常严重。但收入比花费更巨。任粮道两个月后,就支付了部分的欠款和利息,还给家庭寄了八千两。上任八个月后,他从山西到北京再到西安,一路的花费基本上还完了。他粮道这个位置特别重要,就是陋规的来源:交粮的时候,找各种理由来获取利益,比如说粮的成色不好、水分高,要打折,或是把那个斗做得小一点等等。
但张集馨认识到陋规不合理,他采取了几种措施减轻自己对陋规的依赖,第一就是像马克斯·韦伯和黄仁宇研究明代的财政制度提到的复式簿记,公私账目分明,家里用的钱和做生意的钱是两本账簿。然后公事尽量亲力亲为,很少带家人去赴任,减轻吏的人数。第二,他有钱后就投资房地产、药铺、缎号等来获得资产升值。第三就是他拒绝可以不要的陋规。他属臬司的时候,陕西的新粮道还没到任。按照常规他可以继续任,只要多任粮道十天,可以得两万两银子。但是他说既然自己是臬司,就不任粮道了。
4、孤独的大员
他花了很多银子在官场上,跟人的交道也特别多,但结果他在剿捻军受伤后,没有人来看他,他被弹劾时没有人为他说话,所以他特别郁闷。原因是他群而不党,表现在:第一,他对公私混淆的敏感,第二就是他一面积极地应酬,另一面在心底划了一条君子和小人的界线,既近人情又不通请托,认为自己既保持了君子、一种国家官员的身份,也能与其他人打得火热。实际上在清末官场上,这种别敬、喝酒都是”规定动作“,并不能说明他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员,他这种自命清高、鄙视陋习的心态是人尽皆知,很自然地就被排除在外。第三点就是他的士与仕官身份。

三、身份问题:士与官僚
“士”是做道统的担纲者,“从道不从君”,如果不能捍卫道统,宁退勿进,不同流合污。而官僚不一样, “思不出其位”,要切实履行其职责。在天朝体制下,就只有忠心于天子。士和官的冲突就是源于“公天下”的“道”以及帝王的“公”与国家的“公”之间的冲突。张集馨在道光年间处理得比较顺利,到咸丰年间就出现了问题,尤其是第一次被弹劾和免职之后。在僧格林沁第一次表彰他之后,皇帝恢复了他的五品官职,他虽然感恩戴德,但认识到“因人成事”——只有林则徐、琦善和僧格林沁才能给他前途。因为皇帝被奏折牵着走,本身不能做出独立的判断。所以虽然表现尽忠,但态度截然不同,尽忠的衰退导致尽职的表面化。
他处理这些问题主要有两条:“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乾”。“初心”是对“士”的人格和道统的捍卫,而黄老之术是失意官僚应对外界压迫的犬儒主义处对。范仲淹是居高位而“诤谏”不止,张集馨不同,他首先要自保,他的“士”的人格被放到了黄老之术犬儒主义的壳里面,结果是既没有保住他的“士”,也没有保住他的“公”。
讨论:制度和伦理激荡中的公私关系
张集馨的思想来源当然是孔孟学说,但是他受道光年间的经世思想的影响很大,对理学评价不高,这跟曾国藩相反,曾国藩既受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同时也受理学影响很大。他跟海瑞也不同,海瑞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很大,看中一条路就往前冲,不管后果如何。而张集馨最重要的是平衡术,在不同的“公”和“私”之间执行平衡,但他最后的被弹劾实际上标志着他的平衡术的失败。我觉得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文化和体制的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现实的复杂性。各种现实的“公”和“私”的不同诉求带来的压力。但是现实的复杂性并不是独立的“实存”,它是有知识建构的,这在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原始分类》讲得很清楚,有什么样的知识就建构什么样的社会,知识和社会之间相互建构。对中国来说,也就是渠敬东在《社会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谈的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在渠敬东看来,道统是基于夏商周,尤其是西周的想象,建立的公天下,天道、国家、君臣关系都是统一的,以“公”为目标,这个想象构成了孔孟学说的基点。但秦朝以后实际上进入了一个以法家为基础的专制体制,变成了“政统”。虽然瞿同祖先生在《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当中讲到,中国的法律是以儒入法,但以儒入法不是全面的,政统是现实的,道统是理想的,和现实的政治之间始终有某种张力。道统的公天下与政统的国天下,家天下一定形成非常紧张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体制。
而且儒家的道统有它的特点,就是“差序格局”。它是一种自然的血缘关系,家国一体,就是把家的血缘关系引申到国家的关系中去,形成了“尊尊”“亲亲”的关系,这带来两种影响,一个是“父子有亲,兄弟有序,君臣有义”的社会构建,第二个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大同”的格局。这是差序格局的两重理想。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费孝通所说的波纹式的“自我主义”,为了小家可以牺牲大家,为了自我可以牺牲小家。这种差序格局最大的特征是公私不分,恰恰为伦理关系制造了一丁点障碍。古希腊传统中家国的二元格局非常清楚。日本也有所不同,沟口雄三认为日本传统中还是有个人主义的空间,所以公共空间就是一个封闭确定的空间,私人是不能染指的。而在中国,空间具有权力的等级性,没有稳定的边界,不能拒绝私的侵入。这种格局下,张集馨就很难处理公和私、家和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会生产出各种拟血缘的关系,最后就牺牲了公,成全了私,甚至把私也牺牲掉了。这是从差序格局的角度来理解张集馨的这种公私平衡术失败的根本性、制度性和伦理性原因。
那么我们怎么来突破?个人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侯俊丹认为,普遍个体“人格”为心性基础才能开辟现代国家政治,沟口雄三也说过,如何从既定性的伦理立场出发,引出欧洲的个体观念。这和我的观念一样,中国社会首先应该走向个人主义,但是侯俊丹的判断是乐观的,她认为戊戌变法前后的知识界已经认识到个人主义的历史必然。沟口雄三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梁启超那代人的思维中,共同的东西才是最终的,公私关系界定的基础还是“克己复礼”而非对个人权利之尊重。沟口雄三对梁启超的批判我是接受的,但是他认为卢梭的个人主义对中国也有用,实际上卢梭的个人主义有某种伪装的成分。《社会契约论》中公义和选举的关系上,是要让自己和公义合起来,这不是个人主义。从涂尔干在1898年对卢梭的个人主义和康德个人主义的赞扬中可以看出,涂尔干的道德个人主义是相对虚假的个人主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真正英美意义上的个人主义。
问题来了,我要讨论的是儒家伦理和现代个人主义的关系,我们今天谈的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把个人主义作为一个基础,转化儒家的伦理,需要理性细致地检讨传统的伦理规范,彰显各种本土性伦理美德,恰当地发挥其社会规范功能。儒家传统伦理和个人主义的结合,一方面有效地在制度和伦理两个层面厘清公和私的边界,另一方面用传统伦理美德来防止个人主义向原子论以及利己主义滑落。涂尔干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实际上都是围绕利己主义和原子论的兴起来说的,包括8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这种社群主义的兴起,比如桑德尔。传统可以在防止中国向利己主义滑落,但是根本问题是传统不是基础,个人主义才是基础,这是我报告的一个结论。
随后,肖老师与周勇教授及在场其他师生就这一话题所涉及的“个人主义”与儒家“人格主义”、“公”和“私”概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和讨论,上午12点左右,沙龙结束。

现场提问与讨论
周勇教授:我有四点感受。第一,讨论公私思想史的时候,肖老师说没有亲自研究,都是用的二手资料,让我觉得很诚恳,很坦诚地说出来。我也很认同这一点。这两年我们在提到中国现实和历史的时候,老先生提醒我们,至少你前四史一定要去看吧,一直到这两年才理解这句话。我们应该寻找新的概念来研究思想史,超越沟口雄三。第二,肖老师很善于从新的文本中发现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强调从小说、日记这些材料来发现社会学问题。现在要看学科之外的材料,实际上这是很好的经验资料。我很欣赏白鹿原,中国近百年的乡村和教育变迁,教育学术界同样写近百年的教育变迁,没有白鹿原那么生动。《马桥辞典》是一个当代社会的,《白鹿原》是乡村社会的,可以做一个呼应和比较。这是第二个问题,顺着这个会牵涉到,善于用社会学的概念去解读小说,读小说一定是为了社会学目的的。社会学始终是关注共同体,公私关系等社会学的命题,如何呈现和揭示这些命题,而且有自己的概念创造。肖老师有苦难共同体,甜蜜共同体,这个就是以往没有出现过的共同体。就我们的专业提到共同体就会想到托尼斯,或者想象的共同体,文学界的。看似甜蜜的共同体实际上是充满苦难,尤其家庭,中古传统家庭真的是纠纷不断,靠人情在维系,闹得再僵还是父子,夫妻再怎么闹还是夫妻,破镜重圆。肖老师发明的这些概念很适合分析中国经验。第三个是在具体的经验选择上,肖老师在分析家庭领域、官场领域的种种生活,我留意到肖老师关注大家庭的纠纷,官场里的断案、陋规。我想背后是有考虑的,大家一会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家庭里的生活,官场里的生活有很多,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个方面来呈现公私的矛盾,呈现其中的苦难。我想这跟肖老师最开始的判断有关,肖老师说当下的一些社会现象是有历史根源的,当下的事情实际上还是在延续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肖老师关心的这些我也关心,比如在写韩愈的时候,我也在想,韩愈到了长安怎么生活,他的工资很低,他没有陋规,好处费还拿不到,但是他靠给人家写墓志铭,那时候写墓志铭收入很高。这是任何一个时期都可能碰到的问题,不管你是唐代、宋代还是当代,一个人总会面临这些基本的问题,这些基本的问题会涉及到公私。韩愈写墓志铭的时候也很痛苦,违背了道统,不能做这些事情的。还有提到过晚清的官民比例,在当代的中国乡村也存在这个问题,在中国长期的社会结构下都存在。在具体的经验选择上也很有讲究,我们要写生活,我们每个人各自都有自己关心的东西,当代社会关心什么我们就会选择什么。第四个是,如果我们从教育学的角度,用肖老师的材料,我们怎么把这些材料教育学化,我有一个体会,共同体或公私关系都是可以教育学化的,这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的思想难题,这样就很简单地把肖老师的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教育学化就变成了道德教育的范畴,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理论也在处理共同体、公私关系的难题,今天的教育理论确实不大关注共同体,关注的是抽象的个体,从个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其实早先不管是孔子还是涂尔干,杜威,他们是有共同体和社会的概念的,但是我们今天变成了个体出发思考教育,我们今天将教育就会讲从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个体,今天又变成培养有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个体,老是围绕个体发展,就不会把个体放在社会、共同体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当代教育问题在回避这个问题,但是在历史上教育哲学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可以把这个主题教育学化的。共同体、公私关系等还是大的概念,小的概念也可以教育学化的,比如肖老师提到的陋规这个概念,这是中国本土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教育界也有很多,古代陋规非常多,前两天我重新再看胡适和梁漱溟的资料,两个人很有意思。梁漱溟、胡适、蔡先生都在会场上,梁先生听他们讲话,听完之后,觉得他们讲话太假了,讲归讲,做是另一回事,胡先生善于捣糨糊,他就说,梁先生你太认真了。这就是陋规,胡适就精通陋规,所以他在各个领域都呼风唤雨,所以梁先生最后也是孤独离开了北大的圈子。所以很多概念都可以用到教育界,都是可以考察教育现象的。最后一个,在结尾的时候肖老师提到“孤独”这两个字,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新方向,各个学科的学术论文老是没有人间冷暖,看下来像机器一样,如果是纯理性的也好,但也不是真的理性,不知道叫什么,人写的东西结果没有人的温度和情感,肖老师这一点大概也是努力的方向,改变学术论文的味道。学术论文当然要以理性的论文分析,但是如果只是理性的分析,也是有残缺的。为什么小说、电影值得我们喜欢?你看像季风、先锋,摆在最前面的一定是小说类的书,一定不会是教育学类的著作,很难看到,说明大家还喜欢读小说,所以说这个就是既有理性的分析,又有人情味在里边,读了之后会感动。什么时候学术论文让人读了会感动,我想年轻人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做得有点意思。我们也会想年轻人为什么和我们当年的学术状态不一样,也不能纯粹怪年轻人,你想年轻人看了这么多论文也很痛苦的,所以我觉得人情味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方向,文章结束的时候至少底色是有人情,温度的。用“孤独”这个字,很合适,这个让我想到中国的古典教育或儒家教育,总是培养孤独的仕人,优秀的人接受儒家教育很好的,往往孤独。这个我们没有认真去思考,这是个现象,从孔子开始,包括孔子本人,到清代都是这样的,甚至当代受古典教育影响大的人也都都往往有孤独感。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总是培养孤独的仕人?其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肖老师分析到“道统”,我很认同,如果你坚守“道统”,慢慢地你会很孤独,但是中国人有办法超越孤独,这个当然是个体的努力。如果古典教育老在培养孤独的仕人,那么我们就来思考当代中国教育正在培养什么样的人?钱理群先生曾给出过一个答案,他曾说过“包括北大,我们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对此观点持保留意见,如若全部是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我们的教育几乎是可以说是失败的。有趣的是,美国最近也出版了名为《优秀的绵羊》的一本书著,讲述了以常春藤名校为案例的美国教育在培养何种人,所谓优秀,等同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华尔街,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对社会以及公共利益,漠若罔闻,导致美国精英教育陷入误区,美国社会危急重重。这也是一种回答。
其实肖老师自己也给出一种独特的回答,以“个人主义”,尊重个人的新的公私伦理,这也为我们的新的教育理想呈现一种新的可能。对于个人的“失败”,在肖老师的分析中,被归结为制度层面的原因:公私关系界定未明,不可避免的导致士人的“失败”。但我个人而言,我未必觉得以张集馨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是失败的,相反可以在层面上理解为一种“胜利”,在古典教育信仰,和道统的基础之上,这里也涉及到一些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究竟何以界定,以后的方向是来自于一个全新的伦理,还是持守在道德的传统上提出一个新的教育理想,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感谢肖瑛老师,也请各位就历史或者当前现实,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肖瑛老师:非常感谢周老师的中肯评论,第一点,我的整个理论框架多来自二手,特别是沟口雄三,有某种陈旧性和新的理论的出现,同样也给我一些启示,我接下来的工作会聚焦于思想史,做一些使之更为清晰的梳理,下一位个案我也许会做曾国藩,周勇老师对于我的结论也做出一种“另类”的设想和可能性、胜利和失败,更为本质的是涉及到西方个人主义和儒家伦理的关系处理问题,这也是我论文结论中提出的一方面观点,相较于五年之前我的结论看似更为成熟了,有很多观点的共鸣,特别是周勇老师提到了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很渴望将之做下去,白鹿原当中贯穿的陕西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转变的厚重感,我认为鲜有小说能够企及。对于中国教育的理解和反思,我们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渗透了“成功主义”学说,包括校长在内,几乎所有人的演说都在灌输一种“成功学”,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所谓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好,所谓“孤独的士人”也好,需要我们在对人才的教育问题上进行长足的反思和批判。非常感谢周老师的评论。
课程系陆老师:我有两点非常深刻的启发,一是教育研究的温度和情感问题,我是做教师专业发展与课程,强调实证,强调数理的,西方研究方法的引进,如何在实证研究的方法路径中,注入相应的情感和温度,不再拘泥于实证方法统管下的八股文式的研究,得出可靠而枯燥的结论,“低温感”的研究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我最近正在开展生活史研究的内容,关于教师教育研究,个人发展取向应该是很强烈的,诸如教师个人须具备的品质和质素,个人对于集体之影响等等,我在思考如何把教师个人之私与集体之公的分化,例如肖老师研究中“与社会某些团体划分清浊之界限,最终成为董道而不豫的孤独士人”,对于中国教师发展的研究,我们惯常于借用西方研究方法来考察和阐释,但将其置于现在这样一个具有多重的观念交织的新儒家伦理背景下,也许会有很多新的视角延伸。
王独慎:肖老师,我研究的主题是清末民初的修身课,涉及到群己、公私等关系,您在研究儒家伦理和现代个人主义的关系中提到了以“个人主义”作为基础,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请您针对这个问题再谈的深入一些?我所知道的近代个人主义来自于先前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卢梭主义的,一个是弥尔,但是后者被放弃掉了,今天我们还是延续了卢梭主义。您说的这个“个人主义”是否指充分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狄百瑞先生在《中国的自由传统》中提出了“人格主义”,西方可能并不认为中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但是确实存在一种“人格主义”,那么这样的“人格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否可以进行某种沟通?
肖瑛老师:我也读过一本类似的书,也是在谈西方个人主义的,儒家传统下的个人主义,和英美西方文化下的个人主义是相异的,儒家传统下的个人主义被嵌入到一个大的道统的范畴之内,以及与共同体的关系角度去展开讨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穷”之时,个人主义就强烈的体现出来,但当“达”之时,个人主义被人为的掩抑下去,以“身”为中心点向外推进,是一种非常不确定的、有限的、狭隘的个人主义,我们不能说儒家知识分子没有尊严,实际上,儒家知识分子对尊严的追求是通过道统来捍卫、彰显的,它(尊严)是一定存在的。但是中国的这种个人主义与西方的不同,在西方的传统中,个人主义最重要的一点是重视财产权。洛克所有理论的基础,最重要的是私人的财产权的保护,所以他所说的这种文明国家的出现,都是在财产权的保护的基础上来彰显的。财产权的彰显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尊严。其实这一点在《孟子》里面也讲到,就是讲“有恒产而有恒心”,但同时他也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这就是“人格”的一个概念。我们每个人可以以儒家那样的人格为自诩,但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还是一个现实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财产权的扩大就变成了一个个人边界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你怎么看待别人的问题。比如段光清向皇帝的汇报,就是召对的时候,都是“允”,受过儒家训练的知识分子,是士大夫。这实际上是它有很强的等级性观念在里面,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了,谁也不可能说,老师比学生高人一等。所以,它恰恰是在所有权,在人和人的尊严上,这样一种平等的关系。所有权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和人的边界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说的“苦难”,实际上这种苦难性恰恰来自于个人之见边界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讲个人主义,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说的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我绝不是否认儒家的伦理在今天的意义,关键使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来讨论这个问题。要讨论的话,我们要对这个概念做一个清晰的界定,不能简单来说,我们也有个人主义,这种说法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把这个概念厘清,然后我们确定对话的起点在哪里,平台在哪里。昨天我们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带着一帮学生来读。从80年代以来到现在,很多人,像金耀基,余英时先生都在批判韦伯的说法,说中国也有资本主义,儒商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我就说如果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精细地阅读的话,你就会明显感觉到韦伯那个观点是无法反驳的,因为他把概念界定得太清楚了,我们只能在逻辑上和史料上来反驳,在概念上没法反驳它,因为他说的非常精致。我来做这个研究,它从某种程度上,有个方法论的诉求在,这个诉求就是我们怎样来界定概念的问题,只有有了这个东西,我们才能够进行对话。
周勇教授:这涉及到当初这个概念的所指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在借用这个概念。比如个人主义,这个词是个外来词,从清末开始,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变化的。一开始,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词,那个时候政治革命是首要的。到了五四的时候,又偏向了伦理主义,对个体的尊严、自由和平等,胡适代表的“易卜生主义”过来了,所以这个概念进来之后,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界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么它本身在西方究竟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在西方也有变化,福柯这一代人就发现,他在古希腊找到了一种他自己满意的个人主义,美学意义的个人主义,跟近现代不一样,不涉及到政治,不涉及到我跟你平等,它就是一个人自我塑造,古希腊很多自我塑造,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艺术品,这是美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所以当我们提个人主义的时候,这个究竟所指的是什么,你的论文关注的是民国时期的个人主义到底所指是什么。
肖瑛教授:最近《探索与争鸣》第八期,那里面就有一篇文章就是谈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的,就是你们华师大的一位老师写的。
周勇教授:杨国强。他马上要讲做个题目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
肖瑛教授:理学中的个人主义是非常明显的,那种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所谓的“禁欲主义”。不能说我们的传统没有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实际上是要跟现实中间,我们当下立足的,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再来讨论它给我们有什么启示。
周勇教授:余先生写的很多书都很欣赏,但是他写的讨论资本主义与东亚经济的崛起这是胡扯的,完全是乱利用韦伯的东西。
肖瑛教授:我给博士生读这本书的时候,博士生看不出来,我说是把它当反面教材的。
樊洁:您刚才提到,他采用的摆平理顺作为基本手段,得出的结论是表面上的平正带来了帝国制度之“公”的暗地流失。但是为什么这会造成流失,您好像迫于时间关系没有展开说。我觉得是他调和式的一团和气的方式首先侵蚀了法的威慑力,因为法是对“公”的有效维护。另外一个是违法者和违规者的成本,你退一步,我也退一步,这样子,我们都没有损失,造成了反复的违规。您看看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肖瑛教授:你说的和我说的一模一样,的确是这样,法制一定是公,如果法制是私的化,那实际上帝国就不存在公了,因为立法的腐败比执法的腐败严重的多了,这就是最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的这样方式,法的严肃性是得不到维护的,因为(违规)成本非常低,只不过是偶然被逮住了,逮住之后只要把吃下去的吐出来之后就可以了,这个“公”就没办法维系了。当然这个“公”还是在一个帝国的意义上来讲的,实际上张集馨他不仅是对帝国的这个“公”,而且是他对“公天下”的“公”也造成了一种损害。所以,现实和理想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性,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自己是“诸事平正”,觉得他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也是他的无奈,他的无奈是跟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在清末那个时候,他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在宋的时候,肯定不一样。因为宋朝,从赵匡胤到他的弟弟,基本上确定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所以范仲淹和司马光以及王安石的争论,为什么可以继续,是因为它本身有底线,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争,甚至有失败者,胜利者,但是不会置某人于死地,这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好,谢谢你。
周勇教授:感谢肖老师,我们希望下次还可以围绕某一个文本,我们从社会学角度、教育学角度展开一个联合的沙龙,欢迎肖老师下次再光临我们的沙龙!
上午12点左右,沙龙结束。
录音整理:王独慎 童星 张峻源 李悦 郝东辉 曹雯
刁益虎 陶阳 张传月 樊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