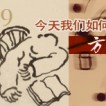主讲:方旭东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主持:周勇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
时间:2016年12月16日 2:30pm
地点: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1711室
周勇:各位老师下午好,今天很荣幸请到哲学系的方旭东教授,接下来我以朋友的身份为大家介绍一下方教授的履历,旭东兄95年在华师大读研究生,师从杨国荣老师,后又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读陈来老师的博士,又到哈佛、牛津去做访问学者,除了哲学之外他还喜欢很多东西,比如文学、小说、电影、摇滚乐,他一方面浸淫于学院派哲学,另一方面又会把自己的关于兴趣所延展的思考渗透入哲学,诸如今天的主题:读经。也许大家对读经各持观点,我们来请方教授来分享他对读经的理解和思考。
方旭东教授:首先非常感谢周勇教授的邀请,与其说我来做一个讲座,不如说我今天带着一个问题来,一个我最近关心的事件,以及事件涉及到的一个争议,我今天采用的方式是首先把事件双方的观点摆出来,在此基础上和在座各位一起讨论。今天的主题:“我们如何读经“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具体事件而来的,回顾2016儒学界或社会事件方面,有关读经的争议应该可以列到十大之一。

“如何读经”的争议双方:
「王财贵」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曾师事隐者掌牧民先生、书法家王恺和先生,是牟宗三先生的入室弟子,也同时是其第一位博士,学术专长主要为读经教育学,理则学,中国哲学等等。
王财贵教授近些年从台湾来到大陆推广儿童读经。此前,其推行的儿童读经在台湾就有过批评的声音,同样,在大陆推行之后也引来了批评和争议,但这不影响其大陆开展的读经教育已渐成规模,特别是2013年他创办文理书院,倡导纯读经的形式。介绍到这里,我来把持相左意见的另一方也向大家介绍一下。
从台湾来到大陆发展的还有一位是龚鹏程,现在在北大中文系,他对于王财贵提倡的儿童读经不以为然,另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大陆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虽然有的人认他不足以代表,陈明也声明,他很早就批评全日制读经,但是这些批评都比较零散,对王财贵的批评造成比较大杀伤力的应该是从2016年始猛力声讨的柯小刚。
「柯小刚」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系主任、中国思想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同济中国思想与文化丛书及《儒学与古典学评论》主编、道里书院山长,创办公益性质的道里书院网络读书会。是一位知名的儒家学人。
小刚当时在上海儒学研究会上发过一个题为《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以读经运动为反思案例》的报告,此前,他曾在上海儒学研究会微信群中跟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当时的回应并不激烈,在2016年5月,他进一步发表了系统性的反对意见,并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然后各大媒体跟进,包括南方报系和澎湃新闻网,很快就发酵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对“读经运动”的反思。大家都有体会,在中国的引起争议的任何事情,很快就能分成两派,知识分子阵营就会站队。争议的发生和后续的发酵如此迅速,我自己也是后知后觉的展开对整个事件的梳理。
柯小刚先是以猛烈的炮火对王财贵发出了系统性,同时也最具杀伤力的评论,事后王财贵也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做出回应。争论的核心涉及到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理解与记忆,以及对传统如何接受等等面向。在我看来涉及到教育最根本的一些问题有关系,教育到底要教什么,我们要不要读经, 以及如果要读,读什么样的经,怎么读。虽然看起来是儒门内的一些争论,但这个事件的意义不止如此,在我自己的哲学视角下,以及在座各位的教育学视角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借此事件做一个学理上的判断。

来自柯小刚的“檄文式”声讨
柯小刚特别针对王财贵的读经运动,系统性的提出了三大弊端,其一是“极端的体制化“,其二是”僵化“,其三是”应试化“。
关于“极端的体制化“的批评,他认为,读经本应是在体制外的,作为课外的补充,而王财贵后期开展的全日制读经班采取了极端的完全封闭性,这种全日制封闭背诵,讲求”每天8小时,连续10年“。(当然,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王财贵的读经运动到目前为止只推行到第三个年头。
再来看“应试化“,根据柯小刚的了解,这样的读经运动也需要一种考试,其形式称之为”包本“,要求学生背诵时录视频以供督查。其次,进入读经班也需要升学程序,经过考试才有资格进入其文理书院,由王财贵亲自授课。但这毕竟是坊间传言,后面我们会看到王财贵的申辩。我个人对于这点的想法,其实不仅是读经班,现今存在于娱乐节目中过五关斩六将的进阶式PK也不失为一种”应试化“。
柯小刚对读经运动最不满的是其提出的第三点——”宗教化“。王财贵被奉为”教主“,家长对其顶礼膜拜,成为一种对于国学缺乏理智,近似于宗教的“迷狂”。
其次,柯小刚对于国学热的观察和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商业性,毫无批判性的迎合当代国学消费,纯粹的商业运作;另一方面,比较草根的读经运动,“从娃娃抓起”,具有一种“极端化为宗教形式的反体制运动”。他对于读经运动的结论是很负面的,无论是其谓“成人式的鸡汤化”的,还是“对抗当代社会激进化”,都未能保持儒学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健康有张力的良性互动。
其实柯小刚也有自己主持的面向白领读经的道里书院,他继续评论道:“国学热和读经运动,恰恰运营在文化革命,商业传销,政治宣传三位一体的社会运动的轨道上”,所以他称其为“读经运动”,并且是“简单化,可复制的连锁读经培训模式,国学文化产业市场”,“貌似属于传统文化,实则毫无古典心性,完全是从属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古典文化消费,国学心灵鸡汤。其制造和传播机制完全走在启蒙式的,景观社会的,大众文化的的轨道之上。”在当时可谓重磅抨击,并带着高度理论性和系统性,将其根源,本质,定性为“社会运动”,并抨击其“全日制,十年,每天8小时的愚昧读经,野蛮背诵“。
听完柯小刚的单方面抨击,不明内里的旁观者一定认为这场读经运动是消极的,愚顽的,柯小刚还在随后的文章中提出“八条质疑”,其问法必然将观者导向这场论辩的反面,其矛头首当其冲针对在“背诵”问题方面,特别是“完全不加讲解的”包本式“的背诵’是否可行,并认为其背诵沦为一种”对于一连串的无意义的音节的机械记忆“,并且对于”将一个孩子置于高度封闭,十年日复一日背诵对其而言毫无意义的音节组,如同“摇头丸的摇滚rap”,粗暴的体制化,荒谬的,最好的读经教师不是人,而是复读机,导致其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发出质疑。那么我们是时候该看看王财贵所倡导的读经运动又是在何种理念下提出的,还有,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背诵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接下来平心静气的去展开讨论。
王财贵的回应:“老实读经”法
王财贵其实曾在不同场合介绍过自己的“读经法“,他认为儿童在13岁之前,其记忆力处于黄金时期,其读经也正是针对于该年龄段的儿童,他提出的第二个说法是“老实读经”,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单纯读经,不加任何的疏注,更别提白话文的翻译,以及通俗式讲解。并且,他主张不应从《百家姓》、《千家诗》这些所谓 “蒙学教材”开始读,此外其“大量”指定至少要达到三十万字。下面摘自是王财贵接受儒家网采访时针对柯小刚的批评所做的回应。有些做了正面的回应,有些也略带遁词,其焦点在于背诵。王财贵道出其提倡“背诵“之理由,他认为儿童期主要的学习能力在于记忆,不在理解。所以要以记为主,所以要背诵。针对柯小刚所担忧和抨击机械背诵的弊端,他辩解道,虽然13岁之前强调背诵和记忆,但是人类理解力随着年龄而递增,到了一定的时候,自己自会有一定的理解。现在的单纯背诵并非不让他理解,而是”其时未到“。他说人之通病就是以自己的情况去衡量别人,成人有成人的情况,儿童有儿童的情况,成人已经到了一定年龄,忘了孩子还小,成人所认定的”不理解就枯燥乏味“,对于儿童来说,是否也存在”不理解就枯燥乏味“?在他看来是未必的。王财贵也因激动而发出了” 重要事情说三遍“式的强调:“我说的是儿童的教育!我说的是儿童的教育!我说的是儿童的教育!”
我们先把争锋相对的观点摆在这里。他们讨论引出一些真实存在的问题——对于儿童,我们是不是要以记忆和背诵为主来教育。
王财贵继续辩解道,他所推行的”老实大量读经“,好比”画龙点睛“,读经是先须“画龙”,要在13岁之前背诵几十万体量的经典,到了一定阶段再来为其解经,也就是“点睛”之时。柯小刚对于这一点的驳斥是“只读经不解经,小朋友鲜活的现实生命失去活泼泼的感悟”。王财贵说,何出此言,你的观点是以人性理论为根据呢,还是教育学实践呢?

争论焦点:是否背诵?如何背诵?
那这里双方就各执一词了。背诵到底会不会导致小朋友失去活泼泼的感悟。王财贵做了一个辩解,如果真是这样,那早就该被推翻。他还需面对一种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读经运动是拿我们的孩子当”小白鼠“做教育实验,如果真的如此坚持十年,孩子“废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王财贵回应道,”其实人生何处不是”白老鼠“呢?现在全世界的实用主义教育,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为期八年的教育实验,然后推广到全世界。读经教育,其实在中国西方都发生过,并非自我而始。
关于“阿猫阿狗都能当教师”,王财贵强调对读经老师的素养并不需要很高要求。并援引胡适曾发表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一文,中国读经的争议在“五四”时就已引发激烈讨论,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新派都反对读经。胡适曾声称“所谓的读经连阿猫阿狗都可以来教“,王财贵隔空回应:是,阿猫阿狗就可以来教。即使只有阿猫阿狗,也要及早进行读经教育。这一点与他对读经老师的功能定位有关,在他看来,读经老师本身不代表学问,因为经在那里,老师不是最重要的。也并非故意来找“阿猫阿狗”来做教师,而是在“只有阿猫阿狗的情况下”也不能放弃读经。况且,他认为,读经并不需讲,讲了也没用,讲多或讲错还可能会妨碍背诵。这样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相对于我们传统读经理念的一种颠覆。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财贵提出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来对历代注疏的讲解对掌握和理解经是有必要的?这也是儒家网对王财贵提出的质询。比如说“简单粗暴”,“ 非中非西”,其中还有“违反教育规律”,更严重称其“戕害少儿天性”。为何斥责其“非中非西”呢?因为中国古代读经教育并不是如此,朱子讲“小学”工夫,是教洒扫,进退,应对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而且王阳明讲的是要蒙学诗文,歌诗,做游戏。西方的教法,现在有华德福,是艺术和音乐的启蒙教育。对此,王财贵的辩护是这样,他承认这不是出自儒家传统,不传统没关系,要看对不对。关于这一点,他这样回应龚鹏程的“闻见之知不必背诵”:所读的经没有属于“闻见之知”的,而是千锤百炼的。
至于对“全日制”“封闭化”“体制化”的批驳,他反驳道,为何不批评少林寺全日制练武,练武可以全日制,读经亦可以。最后他说,如果有一种教育比读经更高明更好,你告诉我,有没有。
关于因材施教,和需要背诵的字数体量问题,是否过度?王财贵辩解说,我讲的这个“老实大量”是“尽量”,“ 尽量”老实、“尽量”大量,即便是严格纯读经的学堂,有的学生一两个月背一本,有的三四个月至半年,跟体制化相比,读经仿佛更“因材施教”一些。
背什么?何为“经”?何时背?背多少?
读经到底读什么?把什么作为“经”?从通常意义 上讲,我们现在学的东西都可以称为“经”,每一门课程上的难道不都是“经典”吗?但是王财贵讲的“经典”更接近儒家“经典”。首先他把经书上升到“民族性”“民族传统”的高度,他说中国有“四书五经”,其实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可以讨论。因为现在讲“国学”,究竟把什么东西看做“国学”?其实并不是那么不证自明的,各方观点也都很暧昧。首先说“国”,这个“国”是什么“国”?一般的肯定想当然认为中国,那么深究这个概念的界定问题,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定义,还是按照“汉族”来定义?就是儒家来定义?如果是按照国家来界定,中国境内有大量的穆斯林同胞,他们会同意只将“国学”限定为“四书五经”吗?更不用说中国还有大批的基督徒。这牵涉到界定的侠义和广义的问题,例如,被我们称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先生,其实他的研究主要在是印度,其重要代表作是制糖史的考证,可见,在这里的“国学”的定义域应该是很宽泛的。再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其中就有“西域学”“敦煌学”等机构,当时引起很多不解,随后他们开设了“经学研究室”,主要研究对象是“四书五经”。因此不难理解,在王财贵眼中的“经”就是“四书五经”。
而他推行读经的初衷之一便是他认为中国人已近全然忘记中华文化。台湾已经全盘西化了,他特别在表述中使用了“牺牲”这个词,有种悲壮的况味,在他触目所及之处,一个中国人打开经史子集,却不能读懂原文,还要靠翻译,这就说明这一代的中国人已经不可能了解深度的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已经被牺牲掉了,我们不能让下一代再牺牲。” 今天在座的应该有很多90后,你们如果需要借助于翻译译文来阅读我们的经史子集,你们是否这种‘被牺牲掉’的感觉?这样的观点是不是耸人听闻呢?这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王财贵选取的经典也有层次之分,第一层次即四书,第二层是《周易》《诗经》《老子》《庄子》等,第三层就是古诗文、唐诗、宋词、元曲,第四层才是蒙学。在这个层面,他和很多推行诵读古典的教育的迥然有别,因为一般认为要从所谓的童启蒙读物开始,但他反之,并且言称“要读大经大典,不要读小经小典;要读真经真典,不要读假经假典“。这也是他提出的“老实读经”中包含的意思。
然后关于古文、文言文和白话文的选择,他认为文言文比白话文是要高级的,白话文可以自己读,何以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教,无非是在浪费孩子的时间。另外我自己在这一方面可以补充一个相应的经验。最近我跟我的孩子交流,他现在也才刚好十三岁,但已经能够反刍他小时候吟唱的儿歌内容,他认为现在回过头来看小时候读的那些童话,“太幼稚了!”王财贵就认为诸如儿歌根本不属于真正的音乐,他所认可的真正的音乐就是严肃的古典音乐,并且贬斥市面上的儿歌有“毒害儿童”之嫌,虽又会惹怒一个行业的人,但其所言也未免全无道理,可能小孩也确实会有这样的体认。
关于才艺方面,王财贵也是较为极端的,他提倡纯读经,其他才艺暂时先不学。其理由是先学才艺再读经对读经帮助不大,而且只能成就一面,他也承认毕竟人的精力有限。随后很多人质疑,只读经就够了吗?柯小刚也强烈反对闭门读经。对于光读经够不够,王财贵说我们可以说够也可以说不够,所谓够是就它的“笼罩性”,经是高屋建瓴的,最为高级也是最为统观性的知识,在这一“笼罩”作用下可以助益对其他学习内容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王财贵对于经的确有其独到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何时读”。他关于读经的时期的划分以十三岁为界,并将儿童的学习阶段划分为幼稚期和成熟期,幼稚期主要应培养直觉、吸收、记忆,所以在十三岁之前,只是读,并且反复读,直到熟悉乃至可以背诵。
第三个问题“读多少”。王财贵强调“大量”,对于读经字数的最高要求是至少要背诵三十万字(中文经典二十万字,外文经典十万字),在遍数上,他认为每部经典至少读足一百遍。在时间上,每天读经八小时以上,连续读十年。这是他的最高标准。但他自己也说这个能做到多少是多少,最高目标能做到那是顶级的。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读。这也是最受人攻击的一个问题。王财贵的意思就是不要理解,只是去背。实际上,我们现在包括在大学里基本上是讲经,不是读经。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在大学里或多或少会开经典选读、名著选读这样一些课,本科生甚至研究生现在也还在读《论语》和《孟子》,但这个可能研究性比较强。但其实我发现很多同学,包括少数研究生,如果原来不是科班出身的,四书比如《论语》也是第一次读。我本人在大学教书,所以我更关注我国大学的经学教育,以及大学对经学教育应持有何种态度。虽然现在我们也有一些通识课,但是我们没有专门的经学课,但在台湾,大学新生要读一年的《孟子》,我在想以后我们的大学可不可以专门开设这样的经典课程,而不仅仅是以通识教育形式,而成为一种常设的经典课程。内容以中国经典为主,同时兼顾世界文明经典。在我看来,王财贵的读经运动并没有柯小刚所批评的那么荒唐,而且经由他,引出一些关于儿童经典教育的真正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推行是有可取之处的。我抛砖引玉到这里,也希望听听大家的讨论。

讨论环节
周勇教授:方教授通过一个争论的事件引发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读经“的探讨,这其中涉及到包括经的问题,经典教育的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其实除了王财贵,民间也有很多经学教育活动在开展,包括在座的小姜老师,您也是从事你可以谈一下你那边的情况,对经、读经和方法也不一样,小姜你能不能谈谈你那边对象、价值和方法。”
小姜老师:很多家长送孩子去读《论语》、《黄帝内经》,小孩皆可熟背。我个人看来,其原因无疑是自其父辈开始的国学热,但作为普通父母, 他们并不懂得区分儒家、道家和佛家,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也没有精力再去学习,所以他们也希望孩子仅仅是浅尝辄止,作为一种课外的国学素养的补充。那么王财贵办全封闭的读经班的初衷是什么呢?是想作为教主吗?
方教授:王财贵对这个问题有个回应:如果大众这样理解所谓宗教,就流于肤浅了。宗教必然是有神作为崇拜对象,然而读经活动并没有救赎和神灵,所以不能称其为教主。至于那些家长,非常崇拜他,他无法去禁止这种崇拜的发生——而我自己对于王财贵初衷的理解,他想培养的是浸淫于儒家传统下的经世安邦之士。这也能够解释其读经教材中不包括佛教经典,虽然佛教是中国三大文化之一,她的顾虑是佛教对于儿童而言,太过庞杂,尤其是许多佛教经典未译为汉文,很多术语是梵文音译的,孩子几乎不可能理解,加之有宗教性在,不适宜过早传授。
彭正梅教授:就个人感觉而言,王财贵的感悟更深一些,柯小刚的批判略显肤浅。实际上在读经的过程中,意义就在其中。人们纠缠于各自的理解之中,就会忽视其真义,至于王财贵等人,他们希望在不确定的社会里“恢复”某些在他看来已经失去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种身份焦虑,众所周知,台湾曾被日本殖民,进而又光复,因而台湾人有身份的焦虑。在上海,同样诸多的生活不确定性,人们把传承千年的经典看作是一种给人心理确定和皈依因素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经典往往被束之高阁,作用有限。而读经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具有复归的意义。就这点而言,王财贵的理解是更加深刻的。
刘德恩老师:是否有这样的假设呢?现代心理学认为,知识是有关联性的,经典中蕴含着某些东西,可能会给人追踪或寻根溯源之感。但是对于“经”所蕴含着与现代生活的关联如今日渐丧失了。正如当年杜威来到中国目睹所言:中国学生读书与背诵像是练习饶舌一般。总体来看,儒家所蕴含的哲思在面对当下现实问题而言,很难取得更与时俱进的处理。但王财贵的观点也是很有见解的,即当人们学经之后,潜在的多样性会增强,因为经本身有“笼罩性”(王财贵所提)——记忆的东西往往只有一面,而人生是多面性的,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哪一面会让我们感兴趣。如果在小时候有一种多面的刺激,可能对我们未来对世界整体性的理解与判断,在统观层次上更有好处。
毛毅静老师:现今学校中的国学教育除了读经,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书法,我以此为例。这两种国学素养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我所了解到,教育部有一个目标是要在近年培养五十万中小学书法教师,为什么下如此大的气力来大规模推行中小学生练习书法呢?如果让一个孩子从三岁开始练书法,从什么开始练为好呢?从颜体、宋体等开始练,还是要回到大小篆等呢?这其实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一个孩子学书法,要从执笔开始学,要在一张全新的文本上去写一个他压根不认识的字,他需要慢慢发展这项技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发展到他成为一个书法家,这个书法家与写字无关,因为执笔方式不同,所以他写出的内容,或者说是书写的习惯,是完全不同规则的技艺的训练——其实这和读经是一样的道理。王财贵说,读经读到十三岁。而一般而言,中国的小朋友学书法都是在学前,一直练到小学三年级,差不多在十岁左右因为读书的压力而中止。我想这和儿童读经的经历大致是类似的。读经到底是为了国学素养的提升还是知识的增长,这是一个难题,因为这涉及到将读经当做正式学习还是非正式的学习的划分问题,我们需要具体分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方教授: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众所周知,上海的艺术教育还是比较普及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三岁开始学书法和三岁开始学音乐其影响是不一样的。正如你刚刚所说,练习书法在古代兼具现实的实用功能,比如通信,记录,但是在现代则实用功能转为一种精神享受,情操陶冶。例如现代社会以钢琴为业者非常少,那么练钢琴就从对技能的追求转变到对自身素养的提升。
彭正梅教授:我认为这更多是多元文化时代的身份认同的问题。现在走出国门的人群多起来了,很难确定到底哪些身份意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这样一个多元的时代,人们对于身份确定性的渴望、对自我的、对生活的理解都不同。以前人们忙着实现现实层面的满足,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出现了某种形而上的渴求或者关怀,在生存中必然有一种天然的癖好,如追问生命的本质等等。西方通过宗教仪式,有一部分人专门主持和提醒他们的身份信仰等问题,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不是特别强,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之一。
周勇教授:那么我们的讨论就指向了到底要读哪些内容和怎么读的问题。我从我的经历来讲,首先是“我为何要教授传统文化”,这里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从个体安身立命的角度来考虑,另一个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去考虑。我从文化的角度讲,在国外与外国学者交流,他们更关注你学术思想中真正承袭了中国文化的那一部分,而我们研读和吸收的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都是来自西方的学术思想,我们其实没有承袭自己的东西。记得此前中华书局要出版一套面向中学学生传统文化的教材,共议要编入哪些内容的会议上,有专家就提出只以四书五经为主,我当场提出异见:传统文化有不同的版本,比如明清和唐宋的四书五经版本就明显不同,唐宋八大家年幼时可不仅仅只读四书五经,他们所吸收的自汉代以来的文史类典籍,也是不可忽视的遗产。很多优秀的传统典籍把经学的道理融入文中,正所谓义理、考据、辞章,其中义理就是经学打下的基础;文章如若想要写好还需大量典故,典故就蕴藏于史学之中;而修辞则来自于文学范畴。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内容,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需求两方面来看。我的看法是,无论读经也好、读国学也罢,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版本,需要挑选其中最好的版本,同时与当今急需的内容相切合,这样的读经才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争论才更具意义。
毛毅静老师:我在想,就是我们在学习艺术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规律:一般而言,如果要熟悉掌握一个技艺需要达到一万小时的练习时间,同理,在背诵中,这一万小时其实大约相当于十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十年”就是指我们需要一个长效的、持续的培养技能的时间。但我觉得不代表这类技能培养一定要大量进入到学校的正规教育体系中。我个人很喜欢练习毛笔字,但是矫枉过正的强制性推行未必是一件好事。
刘德恩老师:我之前有看过一份关于各国人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的材料,其中以色列在全球排15名,其贡献率高达70%,排名非常靠前。而众所周知这个国家比我们要保守的多,即便在现在的以色列,民众不仅要读圣经,还要学会看西伯利亚文,这是否是他们的一种身份认同?
周勇教授:王财贵疾呼的“台湾人已经全盘西化”的言论未免是杞人忧天了,假使教育体制废除经学科,也不用担心,因为把经学科在教育体系中转化和渗透成为了文史哲三科,这是另外一种传承机制。所以不需过度担心传统文化消亡,每个不同的人群和个体对历史的了解和当代问题的理解和需求是不一样的。
方教授:关于毛老师说的童子功,民国时期有一位叫罗祖基的教师,贯通中西,他在写回忆录中写道,小时候功夫是打出来的,背不出来就以戒尺打手,他直到现在都很痛恨那一段时光,却又感谢那段时光。童子功,技艺的锻造,对儿童而言是无非是残酷的,但是客观上来讲,学术理论功底都是从这个时期培养起来的,例如电影《霸王别姬》里的小豆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广西幼专访问学者:我本人是作学前教育的,感触较深,我一位同学的先生在自家开办国学教育班,其中教授儿童从两岁半开始一直到十三岁,一直在读四书五经,已有十多年。我也去听过王财贵老师的宣讲,宣讲内容有积极的一面,不仅有心理学,还有教育学的理论支撑,他融合了0-7岁早教和学前教育的很多教育及心理学理论,当时听了很震惊。王老师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缺失,所以当下应该矫枉过正。我们小时候都在读唐诗宋词,文言文,现在印象还很深刻。我们现在继续在寻找文化和身份认同,这是王财贵所强调的,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了,所以缺失了另外一些东西。
我的同事持反对,甚至排斥,但她的先生坚持在做。这可以作为我们后续追踪的,进行对比研究的实例,来验证下国学到底怎么做对孩子、对文化推进有利。老师们提到身份认同,民族文化这些,我也想起身边的例子。我的孩子的外语老师是广西大学外语教授。他(她)也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出国,也希望他们能带有中国文化的符号,比如书法、武术等中国文化标识的东西。但正规的基础教育不教这些,所以会有很多民间的机构作为辅助将传统文化传承给孩子。关于国学的探讨是无休止的,因此不能马上对它做出评断。我们需要经过追踪调研分析,研究其中的利弊。所以我会继续追踪,今天很受启发。
方教授:今天将2016年的这一公共事件做了一些回顾,将争论的原材料拿出来,引发大家有更为有针对性,也更为独立的判断,我对这场读经争论所持的观点是,第一,以读经为主要形式的传统经典教育对于孩子是必不可少的。第二,王财贵推行的不讲解,不加注疏的读经法,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
录音整理:
张传月,王烁,樊洁,陶阳,王独慎,曹雯,童星,张峻源,刁益虎,李悦,郝东辉,江娇娇,郭海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