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文化与社会学者讲座
政策评估S-CAD方法——背景、思路与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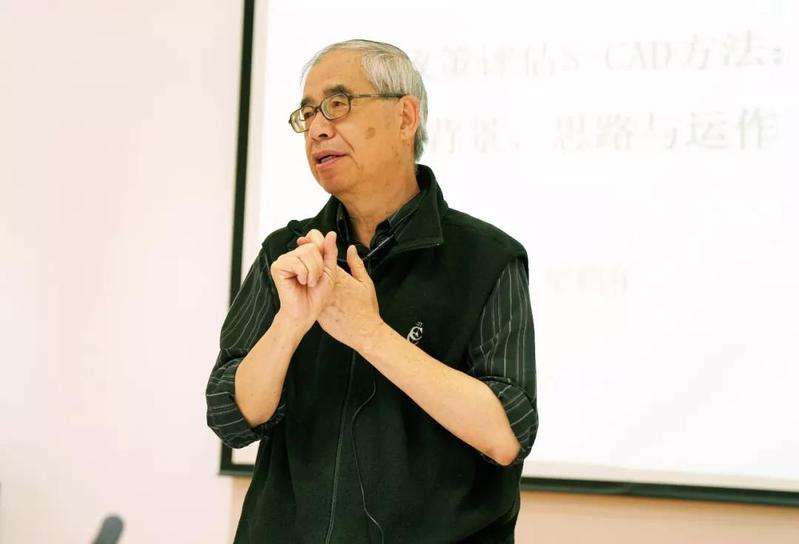
主讲:梁鹤年教授 原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
主持:丁钢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
时间:2017年10月25日14:00
地点:中北校区文科大楼1711

丁钢教授: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梁鹤年教授来给我们做政策评估S-CAD方法:背景、思路与运作。梁教授曾任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1970年毕业于中国香港大学,1976年取得美国麻省学院的城市规划硕士学位,1982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硕士学位,1985年获得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开发与管理博士学位,在土地开发城市与区域规划政策评估方面造诣深厚,其中从1986年开始在城市规划杂支组织相关栏目,发表论文,其专注简明土地利用规划、政策规划与评估已被列为加拿大规划与政策专业学生的教程,同时,他还积极致力于构建学术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桥梁。梁教授在加拿大组织的国家公共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修班在加拿大和亚太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近年来,他在科技、经济、资源等方面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并经常参与国内多个部位地方政府的咨询工作。2002年中国国务院将外国专家的最高奖“国家友谊奖”授予梁鹤年先生;201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也同时被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等聘为兼职教授。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来聆听梁教授的报告。现在,大家欢迎!
梁鹤年教授:
我先跟大家道个谢,因为我是广东出生、广东长大,广东口音,所以听起来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会说慢一点。我讲学的时候习惯站起来,这样就能看见你们的眼睛,你们也能看见我的眼睛,而这样我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睡觉,当然,有些人会睁着眼睡觉也行......
我所讲的内容与PPT并不符合,PPT只是给大家一个感觉,首先,我用五分钟把PPT上的内容过一遍。大概有三个板块:政策评估、西方文化基因、建筑和城市规划。现在国内有六个基地在做我的研究,中国浦东是政策评估的研究基地,另一个是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基因的研究基地有两个,复旦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文化中心;还有我的城市规划研究基地是武汉大学和深圳的哈工大与北大的分院。我1973年离开香港,1970年在香港大学念完建筑,1972年,出于青年的报国心态,希望洋为中用,即自己所学的东西能在中国发展时用上。1977年,我开始重新学习,当年离开香港的推动力就是洋为中用。当时的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时候看见的老外面孔跟现在的老外不完全一样——那时候他们到中国来就像是为了推销东西。我1976年到1977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念书。幸运的是,我是先到美国念书,再到英国来,如果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当年由美国转到英国去的原因是年轻人的虚荣心在作怪,美国麻省理工是在波士顿对面的一个名为剑桥的小城市,因此我就想到真的剑桥去看看,于是就跑到英国剑桥去了。
美国的念书叫“study”,而英国(特别是古老的学校)叫“read”,分别是读和研究的意思。研究就是为用,读为知。在英国的三年是我最愉快的时光,我把在美国念的书都重温了一遍,渐渐发现“洋”不能为“中”用,只能“中为中用”,中西是不一样的;那么,“洋为洋用”可不可以作为研究课题呢?我发现答案是可以的。因为通过“洋为洋用”,我就明白在“洋”的泥土上生长的过程是对这一代人的启发,而非生长出来的东西。他们的理论、工具以及分析如果用在中国肯定会带来一场灾难。If you have a harmer,every thing looks like a nale.锤子是用来锤钉子的,西方的理论就像锤子,而中国不是钉子,是螺丝,用锤子锤螺丝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研究如何通过锤子把手上的力加到钉子上,就可以启发我们了解螺丝转的作用,由此,我们就可以将“洋为洋用”转化为“中为中用”。这么多年来,在国外,大家都说我是个方法论者,是搞方法的,其中一个无法避免的是:我们搞规划的还要了解经济、社会、心理等很多层面的知识,学成之后你就是一个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怎么样把这些集中起来变成一个规划学家,这就需要方法,包括比较研究方法。而不同的方面你不能完全掌握,这就是约束。这个方法论可以用于教育政策,也可以用于城市规划方案,军事,金融,甚至是企业和家庭方面。凡是有目的的行动都是政策,这是政策的定义,而政策有好有坏。

在谈论这个之前,我要讲一个小小的发现,就是西方和东方看世界是很不一样的,不是好与不好之分,而是在做不同的事情,我们有些时候用西方的办法去看,而有些时候用东方的方法去看,怎么说呢?西方倾向于一只眼睛看世界,东方倾向于两只眼睛看世界,有些事情,必须要用一只眼睛去看,例如用枪去瞄靶子,重点在于一枪打中,这就叫效率,如果是一百枪中打中一枪,就不算了。但是,如果你只用一只眼睛把一条线穿进一根针里面,这就很难了。而如果用两只眼睛就比较简单,因为两只眼睛就有两个视角,两个视角就会产生视差,有了视差就会有深度,有了深度就可以看见两件物品之间的距离,而这就是关键。这里面就涉及关系的文化,它求的不是效率,而是平衡。有些时候我们追求的是关系的平衡,有些时候我们追求的是目标,而这就是关键。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探究的问题是怎么样在用一只眼睛的时候做用两只眼睛做的事情,在用两只眼睛的时候做一只眼睛做的事情;当你有两只眼睛时去做一只眼睛做的事情很简单,把一只眼睛闭上就好了,但如果你只有一只眼睛要做两只眼睛的事情时,那该怎么做呢?这就是政策评估方法的起步点。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立意,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有从某一个角度去看。二战时,美国有一个有名的总统,他说:“我坐在总统位置上,很多经济学家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但是我总没有找到一条臂膀。”经济学家每次说一大段,然后接上一句:On the other hand.这对政策的决定没有任何帮助,政策决定需要科学性和专业技术。所以我觉得政策评估时,一要把“一只眼睛看世界”和“两只眼睛看世界”结合起来用;二是要考虑到任何事情都有相关的层面和立意。
政策的好与不好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民族的情绪。每一个政策都会有多方面的批评,我在一本书中写道:每一个决定或政策都有非常多的立意,这是不是就是理性的结束呢?我认为,政治与理性是不应分开的,政治理性就是大家同意了,公众参与了的政策决定等。不同的相关立意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它讲究三点:天时,地利,人和。中国最先考虑的就是人和,它最重要,但不是最先的。方法论者就是想的事情有先有后,有轻有重。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我要从桌子的一边以最短距离走到另一边。首先不能走直线,因为桌子挡住了,它大多时候是不可改变的,这是天时;然后要选择走哪边,这是地利,最后是看桌子的主人让不让我过去,这就是人和。先看天时和地利,再考虑人和是助力还是阻力。所以,它们是有先后的。天时就是效应,是达到目的;地利是效率,以最短的距离达到目的。先考虑达到目的,再考虑成本,之后就是人和,即可行性。也就是说,有效应(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t)、可行性(feasibility)的政策才是成功的政策。这里还没有谈到好与坏,当然我从没有听过一个不成功的政策是好的政策,但还要考虑其他事情,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没有人说,我先有不成功,然后再考虑这个事情,这个是胡闹。我应该先有成功,然后再考虑别的事情。优化-平衡,当你,我现在还没有谈到谁是你,当我要到那里去,这个我是谁啊?所以我说,如果这个我是梁鹤年,那么刚才谈到通过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这个政策是对梁鹤年最好,但不一定是对他最好,但起码对梁鹤年最好,因为它达到梁鹤年的效应、效率、可行。为梁鹤年最好,就是最优化,效应、效率最高。那么对其他人怎么样?相关利益,就是你们。为了过去,我要得到你们的帮助就一定要给你们好处,而当我兼顾你们的利益,我的利益就下降一点,当我的效应、效率达到最高,你们的利益就下降一点,这是肯定的。平衡就是我的效应效率在达到你们的人和条件下是相对最高的,再达到可行条件,就会形成双赢局面,这就是优化又平衡,明白没有?那么对我来说,这个优化又平衡的政策就是最优的,不但是对我梁鹤年好,对你们也是可以接受的,是双赢的局面,是道德的。一定要达到这个水平,不论哪一方多或少一点都不算是双赢,是不可行的。有一点我要请求原谅,有些人认为双赢不是好的政策,那么我要说,对不起,你说什么是好的政策?这个双赢包括的不只是你们,还要考虑生态的利益,这个社会的利益。这个怎么考虑呢?主要是看生态和社会对我这个政策的可行性影响多大。所以这是优化-平衡,是双赢的局面。但是,我要为了优化-平衡,要慢慢从你们的角度去考虑你们要得到多少才接受,这是理性带来道德,这是我的信念。今天我花了这么大气力来谈这个,因为西方的观念里面,他们心里不相信有真正的双赢,因为双方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他们达成共识唯一的方式就是妥协。这当然可以,但妥协是非常虚无的东西,一旦一方改变,最后就乱了。所以这个S-CAD方法就是追求双赢,为什么追求双赢,就是因为如果不是双赢的时候,这个政策就是不可行的。所以非但是妥协,而且是一种推动力。好了,这是这三个理念。
讲完之后,我就谈政策的本质。政策本质上来说,是有目的的行动,行动是策,目的是政。那么什么是好的政策?好的政策是目的正确,行动有效,我相信没有别的定义。在谈目的正确与否之前,先要谈目的明不明确,通过目的的明确,就自然地达到人和,人和就把我们的目的条件都包括进去了,明白这点没有?正确就是非但考虑我自己,也要考虑到别人的利益,这才是正确的目的。所以好政策应该是目的正确,行动有效,但是没有考虑目的之前我们好像马上知道你的目的怎么样,就像之前我们说的那样,好像你知道你的效应、效率,不知道吧?所以先是自己,所以明确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学校的老师们搞政策批评很到家,搞政策评估跟不上,因为很多学校的老师搞政策批评,他不找政策的明确,他马上他进去就是说:你有没有考虑到开发商的利益,你有没有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你有没有考虑到生态的利益?可能我有考虑,可能我没考虑,但是首先来说,你有没有考虑到你的利益,如果我自己的利益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说考虑生态利益?怎么说考虑社会利益?无从开始。好像伽利略说,这个宇宙,你给我一点,我可以把它转动。但是这一点很关键,这一点就是你要追求什么东西。因为这个目的与行动是指你的目的,你的行动,我们评估起来就是你的目的是不是正确,你的行动是不是有效。没有做正确目的之前,我们也先是你是不是明确目的。因为非常多的评估首先讲的是教育,如果你们自己搞政策评估的时候,连自己搞的是什么东西都不清楚,怎么样评搞得好与不好?就好像你们搞博士论文的,我在清华每一年有一个月的规划理论课程,我说:“Research questions are not researchable.”。举例说,城市为什么不断向外围扩散呢?我先找它的道理出来,这个是有能不能research的,城市向外围扩散有千千万万个可能性,有千千万万个原因,你想找什么原因?但是我想找城市不断向外围扩散,我的假设是城市不断向外围扩散是因为小汽车的使用量越来越多,那这个就是。因为你做了个假设嘛。我们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以research questions are not researchable,但是research statements are researchable。然后就是你这个research questions,the answer are researchable。你可能说不存在answer。举个例说,有一个statement是说我的假设是小汽车不断地增加使用,所以城市往外扩散,那你可以找数据啦等等等等。假如你说我的不是这个假设,我的假设是城市电冰箱使用量不断地增加,所以城市是不断往外围扩散的,这是你的假设呀,你可以research,可能证明你的假设是错误的。所以你说你这个假设是错与对的时候,我应该说这不是错与对,应该说这个假设是可以research还是不可以research,那你可以从两个方向看。一个是你的导师,你的导师可能和你说你这个不适当,另外一个是查找文献的时候看看人家是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做一个假设,你就不能再延伸下去,一个question是不能research的。所以我们要先明确你的目的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评估,说你这个目的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上不被人家接受,所以你这个就有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就是行动,这就是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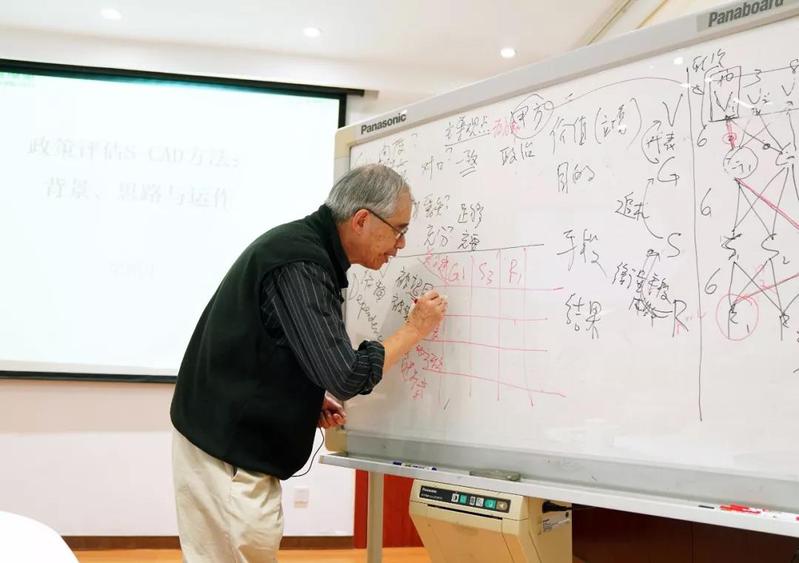
每一个政策都有它的目的,目的后面有它的价值观,这就是立场,这是宏观的。每一个政策都有它的手段,行动是手段,手段下面有它的结果,所以每一个政策都有四个元素V,G,B,R。这个(立场)我叫做V,即value;目的为G,即goal;手段为S,即strategy;结果为R,即result。每一个政策基本上就有这四类元素每一个元素当然可以有非常多的细分,比如B1,B2,B3;可能G1,G2,G3;可能S1,S2,S3;还有可能是R1,R2,R3。所以头一个要做的工作就是把政策的元素抽出来,这是很难的事情,现在不谈难与不难,因为今天不是探讨怎么运作,但是我们要知道,一般人的思想就是,它们的关系就是,目的是用来代表价值,也就是价值的具体化,价值是抽象的,价值观的具体化就是目的;手段是用来追求目的的;结果是用来衡量手段的成败。每一个政策基本上就这四个元素。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我说目的是代表价值观,但是目的放到政策里是代表所有的,有些比较对口,有些不那么对口,因为这些是分不开的。你用这个手段去追求这个目的,但同时会影响其他目的。举个例说,如果你有三个立场,两个目的,那么你有六个环节,明白这条没有?同样来说,如果有两个目的,三个手段,也是六个环节。如果这个(黑板上的),那又有六个环节,所以加起来有十八个环节。十八个环节是息息相关的,好像蜘蛛网一样,我们很多政策比这个还要多。所以我在这配上了软件,把它追踪,什么是追踪,是这个道理,我先把这一边抹掉,我们说我们要考虑效应嘛,效应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目的它代表这个价值,到位不到位,对口不对口,它代表这个对口不对口?对口多少?非常对口?绝对对口?还是一点点对口?或者说是生出矛盾,都可以。追求这个目的用这个手段是对口不对口的,非常对口,还是有相反的效果。对这个对口,但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这个手段对另一个目的是对口还是有相反的效果?他们连起来的时候,效应就是对口不对口,一致不一致,两个是否一致,以此类推,越对口就是越一致。然后效率,这个是代表它需要不需要,充分不充分,越需要的,越充分的,效率越高;越不需要,越不充分的,效率越低。如果不需要,就是浪费;如果不充分,就是功亏一篑。所以效率是需要吗?充分吗?但是不要忘掉你是站在一个明确的目的去出发的,你有一个立场,你的角度是很精确的。假如你这个角度是某一方的利益,那么我们假设是甲方吧,那么我就说你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一些是甲方的价值。如果一个政策出台了,为学生家长是这个价值,如果你是为老师、教育部那就不一样了。从不同方的角度去看它,就是不同的立场,家长、老师,或是某一个老师,可以不断细分。哪一些价值,他们互相的比重是多少,是甲方的事情,所谓甲方的事情就是政策的事情,我们看这个政策对不对。因为每一个政策的评估是有政治的智慧和专业的知识。政治的智慧说我们是这三个立场,说我们暂时定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第二重要,这个是最不重要,选哪一个立场,给他们的重要性相对的多少,这是政策的决定。下面对口不对口是技术的决定,跟政策没关系,它对口就是对口,不对口就是不对口。只要你站稳这个立场,如果你打分数的时候,你站在某一个坚定的、明确的目的上,每一个不同的人打的分数都是一致的,因为什么?因为假如你的角度一样,有什么理由看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呢?你现在看着我,如果我叫你站起来,你看到的肯定是和我一样的,唯一的不一样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你的经验或者技术水平不一样,但是经验和技术水平是可以沟通的,只要你的立场相同。不可能说价值观上我们去打架,同一个价值观,那下面技术的东西是没有界限的;另一个是打分的松紧不同,但松的是所有的分数都松,紧的是所有都紧。政策的东西是你的角度是怎样,就是你采取哪一个观点去看事情,如果大家都是同一个观点去看事情,你没办法看出不同的东西,因为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唯一不可能的就是经验不一样。但是你在价值观一样的时候,经验和技术是可以交流的。那么在我这个方法上,S-CAD,S代表subjectivity;一致性就是C,代表consistency;充要性就是A,代表adequacy;达到最对口、最需要、最充分就是最高的效应效率,当然这个最高的效应效率要在现有的成本下去做,你不能说我是一个神,这就没有意思了,你不能改变现有的条件。所以来到D,D是可行,代表dependency。D就是这个政策被认同、被接受的时候要依赖某一些相关利益。我不是说先优化后平衡吗?所以要知道最重要的立场;哪一个目的最能代表它,最能代表它的当然是最关键的;这个最关键的目的下面哪一个手段是最对口就是最关键的,然后就是分数最高的。也就是说,我是用相关利益认同我这三个东西,我的相关利益接受这三个东西的时候,效率就是最高的,不接受的时候,效率就是低的,明白这条没有?所以关键的政策元素,下面是关键的利益。举个例来说,这是教师的利益,这是家长的利益,这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那么你就用和刚才相同的办法,如果甲方是教育部,刚才谈效应效率的时候我们都是把甲方教育部的帽子戴上去的,那么现在把这个拿开来,我把老师的帽子戴上去,从老师的角度,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还是面对评估同一个政策,去看看他们对G1的看法怎么样,举例来说,假如是10分,0就是无关重要,加是赞成,减是不认同,那么加越多就代表越赞成,减越多代表越不认同。现在从教师的角度,他们是0即不关心;再把教师的帽子去掉,换成家长的帽子戴上,可能是加3,加7。最关键的元素来自于最重要的价值,怎么处理这个?把最高的效应效率下降一点,或者我在这个加一个手段给他,或者在这个减一减,那我这个效应效率就第一点,那么他们的利益就剩下来,给老师的利益就上去了。所以是有三个处理的方法,天时是一个应势,地利是要选择,人和是要处理。三个典型的方法来处理,一个是说之以理,就是对老师团体说,按道理我要对这个G1做政策评估对老师您的利益影响不太大,也可以说就是做工作吧;可能不一定成功,那就诱之以利,在这上头我加一个S4,我的效应效率下降了,但是你可以从S3、S4里面得到好处,而我的(利益)下降一点,对我没有好处,就可以说是收买你吧;然后不成,那就教育部来压之以力,就是用力来压你,当然这个压是有成本的,可能不是这个政策的成本,是从别的政策的成本,主要是这三个方法来处理人和的问题。所以我说,这就是dependency,S-CAD,你一定从一个S出发,这才是评估,才不是批评。能够通过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教育最高效率,C跟A,这几个下面,决定了它的优化。就优化过程来说,我们要知道哪些是关键需要优化的东西,最高分的地方。然后在最高分的地方去看不同的相关利益,从他们的角度去看,然后决定是理,还是利,还是力。我认为,如果你们达到协调的时候,你明确了立场的相对重要性,就是正确。正确就是你兼顾了他们的利益,而且是有理由地来看,这个做法就是知己知彼。可能博弈还是离不开的,就像打牌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牌,能够估计别人的牌,你可能打得最好。但是在这个政策范围里面,如果这个政策所有的参与者每一个人都知道并记住自己的牌,每一个人都尝试去估对方的牌怎么样,那么这个牌气就是最好的。这就是政策的博弈,虽然是博弈,,但是是最精彩的博弈,而不是不伦不类的博弈,所以这是积极的。一个厉害的赌徒不是每一场都打赢的,也是不可能每一场打赢的,就算他每一场都打赢,都不一定是最好的赌徒,因为他有可能只是幸运。最厉害的赌徒是,他有好牌的时候赢得最多,他有差牌的时候输的最小。这一个就是鼓励参与政策博弈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他知道自己的牌,系统科学地来估计别人的牌怎么样,然后去打牌。那么这个国家的政策水平就提高了,没有浪费。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互相之间知识是没有差距的,很容易就变成意识形态上的事情,就变成打无谓的战了。如果你想通之后,你就发现原来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这套方法用一个最简单的四个词让大家记住,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中国在考虑政策决策的时候记住这四个词,就是:立场,手段,目的,结果。
如果用这个来思考,我的手段怎么样?我的目的怎么样?我的立场怎么样?同一个。然后你追求什么东西?效应,效率。凡是所有思考政策的时候,我是考虑效应的问题还是效率的问题,还是考虑可行的问题。天时,地利,人和,其实这些是相联的。这七个词,就是四词真言配上中国的传统,那么你的政策评估就到家,更到位。谢谢!

那么以下的几分钟,我就把整个ppt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样?我就不说这么多了……这些真的不谈,有关理论,什么是理论……那么主要看到下面这句话:政治智慧指导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检验政治智慧,定性指导定量,定量检验定性。主要是政治智慧与科学理性要结合起来。优化-平衡,先评优化,后评平衡,就是先评效应效率,后评平衡……立场是政治的东西,立场的比重、选择是政治的东西,下面的立场与目的的关系就代表吧;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是,就追求吧;结果与手段的关系是衡量吧,这就是技术的问题。你先把你的价值观定在一点的时候,你才可以考虑技术,但是考虑技术之后,你可以重新回到价值观上,所以有先后,因为我们脑袋不能同时思考……所以它的依据就是效应、效率跟可行……
那么下面就给大家一种感觉哈,先是提炼政策元素,包括了政策文本,包括了跟甲方去协商,每一句话都要提炼,每一句话都只可以做一个事情,如果它是立场就不能同时是目的或同时是手段或同时是结果;如果它是手段就不能同时是结果或立场或目的,所以每一句话都是带着独立的一个元素。听起来好像不容易,但如果你做了一两趟,你会发现是很容易掌握的,因为它们有先后级别,立场是比较抽象的,目的比较小抽象,手段更加具体,结果是很具体,所以你给它排出来。先是文本角度,标注每一个元素,然后把元素聚集起来,把有关的信息抽出来,把元素归并起来,然后高度提炼。你看文本那头,来自哪一篇那一页,因为科学的东西应该可以追踪可以重复的,把他归纳起来。所以通过归并,出现下面的两个立场:稳定发展,科学控险。那么这是我们的开始。开始之后,所以这个是……元素,有V,有G,有S,有R。分数下面那个一个是8,一个是6,这个是政策的决定,你可以用表,也可以用图,表示这个样子,图是这个样子,然后开始评了,是把它打分,这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了,对口不对口,要把理由列出来,因为以后可以追踪,如果大家不同意,就可以在经验上、技术上精进,所以……分数打好了。然后就加以评估,每个政策下面的V是为不同的政策来服务的,刚才我们不是说V1是8,V2是6吗?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当我们把整个蜘蛛网连起来的时候,这个效应是不是就反映V1-8、V2-6的相对重要性呢?我们效应出来的时候,前面这两个数是政治的决定,下面这六个是技术性的决定。那么你看8与6.5好像反映8与6的重要性,这个政策的目的还是不错。但是到了政策的手段,这个7.2跟6.3的比例与8跟6的比例不一样,这就是说V1一个比较重要的价值,它的效应明显下降。所以他们最理想的比例是8比6,这就是我们评估的一种结论。还有环节评估,什么分数是最高的,什么是最低的,哪些是负面的,我们一一要把它说明。链条评估,就是我刚刚说的,哪条链条,它们的分数是多少,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见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相应系数,还有一个就是门槛,就假如我们所有的门槛,就是价值——这个价值是可以改的——都定成6的时候,哪些达到6,哪些超过6,这是一个典型。这就是效应评估。刚才是一致性,现在是充要性,同样的,都一样,逻辑是一样的好了,充要性、充分性小结。可行性,先是找出关键的元素,一致性的关键,需要性的关键,充要性的关键,然后这些关键的元素,从主导的观点出发,这个关键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个,这是相关利益。这是我们发明的,从主导观点出发的,戴上他们的帽子。然后,提出处理办法,就是刚才说到的说之以理,诱之以利,压之以力,然后就评估。评估就包括把元素抽取出来,原则是知己知彼。所以把主导观点一定下来,就可以把科学理性用进去了;然后有了双方观点的时候,可以把政治智慧用进去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是把两个混在一起,就永远跑不出来。……
这本书是人民大学上语出版,就我85/86年出版的这个书,就中国普通干部学院一个老师把他翻成中文,是上语出版的,作为他们公共管理的一个经典丛书,从英语来说就是“toward asubject approach to policy planning and evaluation:comment-sense structured”就是都是comment-sense,但是我用方法去把它的结构系统化,这是方法最主要的,我不是说吗?方法就把所有的东西按轻重、先后分开放,把急需做的东西放在一起,这就是方法。四个元素,效应、效率、可行性评估。我们这个软件是免费给你们用的,但是有一个,这个中间要去帮着你怎么用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也是人家免费帮着我去开发的,我发财就没有机会了,朋友还有一点。看,案例你把它放进去,打分,刚才我看见的这三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比重,下面这个1、2、3,和这边的1、2、3,就是效应评估的结果。谢谢!

丁钢教授点评:
非常感谢梁教授!梁教授给我们讲学,首先他自己也有一套方法,而且这套方法在国内也是为人所熟知,这套方法我们也的确感觉到大家会有兴趣。因为实际上国内不仅仅是教育搞政策,更多的是一些政府等其他方面来说。对我们教育政策来说,因为华东师大做得好像也比较多,但我想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因为如果教育的政策,哪怕就我们学校的政策,其实任何政策都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就是一定要考虑完全不同的利益阶层的,就是他完全不可能用一个选择、一个价值、一个利益去做这个政策,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公共政策也就是要兼顾各个方面的。我觉得梁先生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在这个过程中,对政策的议论远没有方法重要。在国外也有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方法大家都要用,而观点不一定要用,这是见仁见智。而我们在做政策的时候对方法其实是关注得不够的,比如说我们在做教育政策这方面,我极少看到有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的,光搞懂数据还是不够的,因为那是科学的东西,像是数据库一类的,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数据库的数据你怎么利用。当然第一步是你这个数据库的数据怎么得来的,一定是从科学来的抽样调查来的,凡是不是这样的,你根据什么文件去搞点什么要素或指标,那都不算的。在研究政策的过程当中,比较缺少方法,议论到议论,那么我们就无法保证所谓的科学真实。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梁教授来为我们讲解他的一些经验,以及通过长期应用检验的方法和理论,这些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所以我们看看,还有点时间,我们同学有什么问题请教梁教授的。

学生提问1:
梁老师你好!我是社会学的学生,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请问,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在政策评估的之后,有一些环节是不符合我们比较良好的状态的话,就我们最后的那几个目标没有达到的话,就只要改变其中的一个链条就可以,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会不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有时候某个改掉链条的时候,就可能改掉全部的链条了,也许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来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可能比较偏理论,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情感与理性,我听您的意思,刚刚提到的理性不仅仅是传统的理性,也包括理性,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情感它在理性中的一个位置。

梁鹤年教授:
好,谢谢!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我这个方法非常重要的考虑,因为每一个环节的改变都能改变整个政策的效应和效率。所以现在不仅仅是政策的评估,还可以作为政策的选择。因为每一个(环节)改变的时候,下面的影响你看不出来的,但是一定要计算出来才算的,所以通过这个方法你就可以追踪,这个影响是哪些修改造成的。因为我说科学的方法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一是可以追踪,二是可以重复的。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得到相同的结果。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感性的的,我是研究有关西方文化的基因,这有一本书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可能有些人看过,《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国外的畅销书,现在已经出了第六版,是14年的。这里面我谈到追踪西方两千多年的文化,过程怎么样,文化绝不是代表看看电影看看书看看小说,不是这个意思的。所有的文明,文明就是我们看见的东西,文明是现象,所有的文明的现象下面是它的文化,文化就是他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些。而且它是有方法的,就是现有宇宙观,然后有伦理观,再有社会观。举个例来说,假如你相信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那么你怎么做人就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按宇宙的秩序,一个是不按它;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宇宙是有秩序的,那么你做人就有很多的另外一套不同的原则。如果你说宇宙完全是偶然的,那么你做人也应该完全是偶然的,不然那时候你就是性格分裂,因为你相信的东西和你做的东西是两回事。当然我们非常多人是不完全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做人有的是有一点性格分裂,有的是糊里糊涂,这是很典型的。在这个书里面,我提到了两条,自从宗教改革之后,就是现代的开始,西方以宗教改革作为现代和现代前的分水岭。宗教改革是1517年,那么过去还有五百年嘛,这过去的五百年是信仰为书,信仰远远超过宗教;二、理性为书,理性远远超过科学,就是现在我们谈的经验科学。经验主义的科学是很假的,当初谈经验主义的洛克很清楚地说明了,它处理得事情不是真理,是仿真理。就是应付过去就可以了,因为经验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某些问题,但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非常多的问题。举个例来说,我们是搞规划的,规划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用经验证明的。比如说,我相信有未来,那哪些经验证明了未来?没有经验证明了未来,所有的经验都是证明有过去。所以理性跟信仰是很相连的,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先有假设再有证明,这个假设就是一种理性、一种感情,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先有定性的东西,才有定量的东西,定量为我们检验定性,定量不能产生定性,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经验都是很有限的,举个例来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过去大概有两百年左右吧,有启蒙的影响,包括我在那里,都是五四运动等等的出来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你以什么样的经验说地球是圆的,围绕着太阳转?明明我每天早上我看见太阳从这边升起,明明每天晚上太阳走到另一边,你还是坚持地球围着它转的吗?我是看了别人的书,看了电影、杂志,就相信了他们。如果你真的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哪一个经验告诉了你地球是动的?没有的。所以我说,刚才说感情就包括了想象力,我们通过我们的想象力,假如地球是动的,那么我们就找证据了,去检验这个假设。现在我们这个假设是非常可靠的。所有经验科学都是falsification,就是每一个证明都有对的,只要有一个证明是不对的,这个科学就掉下来了,但这不是代表科学是不对的,这是代表我们要不断的去证伪,现在你们做论文特别是社会科会这方面的论文,可能我们先来个假设,这个假设是null hypothesis,其实你是证明这个hypothesis是不存在的,所以不是去证明这个东西是对的,而是证明这是不对的、不存在的,每一趟证明都不能推翻,每一趟把它稳固稳定,增强我们的信心。所以你刚刚说的感性上的,感情啦和理性是分不开的,起码在经验主义之前是分不开的,如果你有感兴趣的就看看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我们很多时候认为科学的东西就是理性,其实不是的,理性就是真理产生耐心,如果感兴趣我有另一本书,《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但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是最关键,没有一篇文章用非常长得篇幅去介绍这个概念是什么东西,把它运用到城镇规划上。举例说,我谈柏拉图的永恒,什么是永恒?亚里士多德的变,什么叫做变?笛卡尔的天赋理念,洛克的自由……这些事什么东西,怎么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是很重要的。有句话是英国一位有名诗人说的:“the heart has reason the reason knows not”所以西方人是用脑袋思考,我们是用心来思考。所有的理性是心有理,而一般的理性是没办法明白的。

学生提问2:
刚刚听了这些我的感触很大,回到现实我感觉我们想的很多东西是难以付诸实践的。我其实想问三个问题,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所有的东西其实回到中国的道家来说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而这里面会涉及到我想问的两个问题,一个从我个人的专业角度来讲,它的跨学科,我们所谓的跨学科已经变成了三生万物的横向语言的对话,它本质上是来自于一的,然后在这个融合里面我其实是存在困境的,因为我是跨学科进来的,然后我是存在困境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从政策的实践上我也是存在困境的,回到政策上来讲我们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回到最后其实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去得到一个共识,这个部分上我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困境我们无法实现的就是,到下层的语言对话里它是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个不同的话语体系在对话的过程中必定会存在误解,然后这个误解就像西方的《圣经》里讲的通天塔一样,你永远也无法讲清楚一个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机会出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问在这个问题上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
梁鹤年教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大家听清了这个问题没有啊?(听清了)。你虽然说是道家,但是其实在目前的西方来说,这是xxx。就是我们外语的体系是不一样的,哪来的共识?那么我们要分开两个层面,一个是言语问题,一个是有没有共识。除了言语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去找真相、真理,这个很关键。因为言语是相对的,你说了一个字,才可以说第二个字,才可以说第三个字,你不能像音乐一样同时发好几个音。我有一个老乡,是家里面比较聪明的,他说如果我们说话可以像音乐,像五线谱一样可以同时发好几个音出来的时候,我们视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每一刻只可以发一个音出来的。我说了这么多,为什么要xx的讲,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绝对的东西。如果没有绝对的东西,肯定是没有共识的,只有绝对的东西才可以有共识;如果没有绝对的东西,你可以有妥协,不能说是共识,共同去认识它。我非但是相信,甚至某一个程度上我可以证明,一定是有绝对的。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绝对的,那就什么东西都没有标准,关键就是怎么样去把它找出来。如果你相信宇宙有秩序,那么宇宙是绝对有秩序的,不能有些时候有秩序,有些时候没秩序的。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的?相对就是,现在我这个话可能说得很不好的,如果一个人跟你说这是相对的,就是代表这个人不同意你说的话,所以相对这个词是用来避开讨论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说过他同意你,这是相对的。所以你要明白他后面的动机是怎么样。我们从西方来说,因为现在强调相对,都是凡事相对地,那凡事相对就是绝对了,没有一个事情不相对嘛。我们有时候把相对误解,相对不是比例,比例不是相对,如果我们说某个人做的事情百分之七十是对的,百分之三十是不对的,这不是相对,当你说这句话、想这句话的时候,你的脑袋里他是绝对的百分之七十对,百分之三十不对。你不能同时说他是百分之七十对,百分十三十不对;同时也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不对。所以我们不能把比例当做相对。相对是来自于哪里呢?相对是来自于绝对,凡是因为史、人、事、时、空改变的东西就是相对,不因为史、人、事、时、空改变的东西就是绝对。你看,圆周率是绝对的,不因为谁说了、谁听了而改变。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这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关键就是绝对与相对的分离,如果你不接受绝对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立脚点;你接受绝对的时候,你可以被证明。或者我说,假设和求证嘛,这个绝对是对的,这个绝对是错的,这个你可以证明,因为只要你可以得到验证,但是如果没有绝对的,那么你就无从说起。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生的决定,你可以按完全相对来作为人生标准,但是如果你这样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很有名的,不谈宗教,只谈非宗教的看的,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它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一个道德逻辑来做事情,就绝对的原则,它就是说你先假设你用这个原则,你假设所有人都用这个原则,在这个假定上,然后你假想你愿不愿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如果你愿意的时候,这非但是你应该有的原则,也应该是你希望所有人都有的原则,不然那时候你一定不应该用这个原则,也不允许别人用同样的原则。举个例,如果我的原则是我要欺骗别人来拿到我最大的好处,那么你假设全球的人类都是用同样的原则,你不能说我用你不能用吧。那么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以欺骗别人来达到自己的最高效率,这时候,这是个怎么样的世界?你愿意不愿意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如果你不愿意,那么你这个原则是不应该使用的。所以在这个想法上面,中国也好,西方也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如果你欺骗别人,你可以呀,但是你不能说你不允许别人欺骗我。所以这一些是说绝对与相对的分离,这是categorical,就是绝对的原则,你不能离开它,当然你可以离开,因为人是有天生地一种性格分裂的,我们说的、我们做的和我们想的都可能是有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非常多的人有困惑啊?这个困惑是天谴,是避不开的,因为如果你天生的有性格分裂,但又不困扰,哪来人生?如果你不困扰的时候,你不能允许自己有性格分裂,这怎么讲呢?英语来说:“you cannot have the cake and eat it too ”就是你不能在有一个蛋糕的但是又同时把它吃掉,因为吃掉就没了。因为人是需要条件的,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是生存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的,这是不能避开的。所以我希望这能给你一点思考的方向。

学生提问3:
梁教授,我想问下类似于博弈论的这种东西具体的操作方法;第二个我想问的就是您刚刚说的层次分析的之类的方法是要把各个群体的主观因素考虑进去的……
梁鹤年教授:
我这个方法是元方法,是metamethod,你可以把非常多的其他方法放进去。举个例来说,如果你要给一个环节打分的时候,它对口不对口,你可以通过专家评估、风险评估、成本效应评估都可以,关键就是,我这个方法和其他方法的分别就是你请专家来对这个研究的时候是针对性的,是针对这一条的,而不是针对所有东西。我举个例,因为我是搞方法的,所以这趟没有大概来谈方法,不同的其他方法,其中有个非常有名的方法是成本效应分析。成本效应分析当然可以用在我的方法里,但成本效应本身来说是一个外在的方法,为什么呢?我先举个例,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70年代。70年代的美国有个非常大的运动,之前政府收买了非常多的土地,准备盖公路的,大概那个时候出现这个公路计划,那个时候波士顿有一串的土地就已经被收购了,那么现在不建公路了,用来干什么东西?非常多的方案出台。这一段刚刚是通过一个贫民窟,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反对,市政府就请麻省理工的商学院做一个成本效应分析,分析结果就是效应远远超过成本,所以这个方案是应该正确的。当地的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就请州政府出头,就再做了一个成本效应分析,也是请麻省理工的同一个团队去做,结果是成本高于效应。然后州政府就不服气了,就请联邦政府出头,也是请同一个团队,结果是很难说,成本效应差不多,为什么?因为观点不明朗,价值不清楚。如果作为一个公园来说,是成本还是效应?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可能是效应;对房地产开发的市政府来说就是成本了。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方法用典型的西方用处来说,就是垃圾进来,垃圾出去,非常多的数据,多少钱、平方,但是谁说房地产比公园好?谁说公园比房地产好?就是先有个主导观点,先有个价值,然后才一条一条的算出来。我们的评论是政策评估,不是政策批评。所以你刚才提的题目,有非常多的方法,无论是访谈也好,还是什么别的,你先要把人家的立场弄清楚,不然你问任何一个问题,对方都可以给你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有效还是没用,你不知道。所以我们搞教育,要实实在在追求哪些东西,如果你说你不知道要追求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怎么做呢?我们假设你追求下面三个立场,你重要性的排序是这样的,那么按这个算出来给你看;那么我们把这个重要性倒过来,我有算出这样的答案。这是技术、人要提高政策水平的一个最佳的方法,不是说我要辨认出你的价值观对,你的价值观错,先要拿出证据来。你的价值观这样嘛,好吧,那这样下去就是积极。当它积极的时候,好像人家说是,你最大的敌人可能就是你。当你往镜子里一看,你这个面孔是不好看的,就是你的面孔、你的价值,但是要看这个镜中人那些方法,因为这个镜中人不是你。如果我站在镜子面前,我看那一头的,不是你,而是你的镜中人,很关键的就是你方法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跟镜子里的人飞手,镜子里的人也跟你飞手,你飞的是右手,他飞的是左手,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帮人系领带的时候,走他面前来系是很难的,要走到他背后好像给自己打领带一样来系,因为镜中人和你是不一样的,跟对面的你自己是不一样的,好像一样,但是不是一样,这也是方法。谢谢!
丁钢教授:
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刚才梁教授也为大家做了一些解答。其实你的立场,你的观念的取向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可能还比较关注结构分析、HIM式的层级分析这类的东西,因为层级分析那是很高级的东西、手段。如果你要用多样回归啊之类的,其实一篇文章你也会有很多的表达;但是如果用层级分析来,可能你做出来就是一张表,建了个数据库。但是这个还是仅仅在技术层面上,你要用工具来,不能倒过来把应用工具看做是发文章的手段。其实最重要的,就像梁先生告诉我们的,怎样去评估一个政策,怎样不让我们的工具去代替我们的政策研究,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想今天实际上对我们关心政策研究的同学有启发,有益于启发大家的思考,也给了大家很多的思想。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梁教授!
梁鹤年教授:
从工具来说,用英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应该是a problem looking for a solution,而不是a solution looking for a problem。我们有了工具,就找一个怎么样用这个工具可以做的事情,这是典型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多是a solution looking for a problem,我们有大数据,有solution,但是where is the problem?所以这就从这里来看。谢谢!
录音整理:赖慧、谢婉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