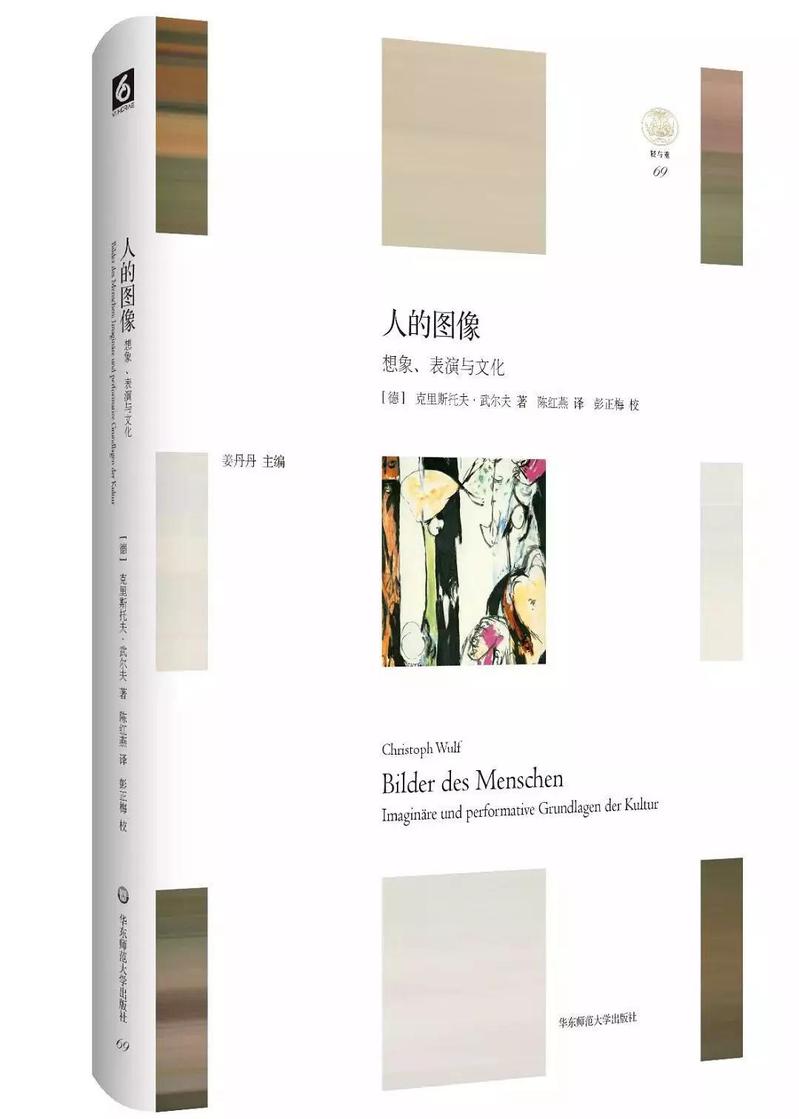
[德]克里斯托夫·武尔夫著、陈红燕译,人的图像:想象、表演与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世界被把握为一幅图像。”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
上个世纪,阿比•瓦尔堡开创了有别于形式研究的图像文化研究,而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确立、米切尔的“图像转向”以及布布雷的“图像的生与死”等命题相继生发——这些图像研究一并随着相关学者走向前台,也使视觉文化研究成为显学。
另一方面,可视传媒的迅猛发展、拟像对真实图像的僭越以及视觉奇观的涌现,使得学界愈来愈正视图像研究在当今视觉文化时代的重要性,并开展了学科内及跨学科的诸多研究。但教育学在这一大潮中却步履迟缓,在图像教育的研究中长期缺席或姗姗来迟,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作为其中之一,德国自由大学教育人类学教授与历史人类学杂志创刊者克里斯托夫•武尔夫便写下著作《人的图像》以呼吁教育学界对此领域的重视。而随着其中文版于今年10月面世,它无疑会成为国内教育学界的宝贵资料。
本书与作者发表在《基础教育》中的文章立足点——人的形象1稍有区别,但殊途同归,都在为图像教育建言献策。在此,我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这篇文章,作为阅读本书的前瞻。
在《人的形象与图像化》一文中,武尔夫教授就梳理了形象的演变史,并指出其政治社会功能,特别是在联合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框架后,作者认为“教育将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完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教育, 就无所谓可持续发展”;而目前, “国际社会正在寻求一个全人类、全社会、所有文化都能接纳的人的典型形象, 一个能够囊括文化社会多样性的人的形象”,由此作者将形象教育的重要性带了出来。并接着论述其重要性:它体现于形象作用于儿童的成长,是儿童模仿学习的重要媒介;同时,它是个体社会化与主体建构的重要途径,并且长期地、持久地作用于身体,作为身体固有的一部分而存在。
那么,如此重要的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呢?作者认为,它是通过想象力与形象的双重作用予以建构的。这里的图像不仅指的是为视觉所捕捉的图像,还包括所有感官获得的知觉图像,包括回忆性图像、愿景型图像、梦境图像等;由而“它(人的图像)将客体对象、行动世界和他人世界转化为图像形式。运用想象力,使它们想象化,从而转化为集体和个体想象世界中的一部分。”并且,“这些过程很多都是模仿性的,都是出于对他人、环境、观念、图像同化的结果。在模仿过程中,外部世界进入到内部,进入到一个充满了图像的想象世界。而反过来,这一充满图像的想象世界又塑造了外部世界。”可以说,想象力与图像互为手段,彼此合谋,通过个体的“模仿性学习”而塑造了主体形象,进而也推进了主体社会化与行动方向。由此,图像的教育功能浮出水面。
而“想象力记录、创造、连接并且投射了各种图像,它创生了实在。与此同时,实在又协助想象力创造了图像。”可见,正是在想象力与图像的双重作用下,社会化与主体化的形象建构成为可能,甚至于社会本身都需要通过想象力而构建;通过勾勒未来图景,形成内在图式,形象的“述行性”便成为图像权力的直接作用点。所以作者在末段指出“图像和想象力对我们构建与世界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 以及与我们自身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正因如此,学界才需要冷静思考。图像在发挥正作用的同时,也将暗面一并带到场域中。所以教授强调“我们也需要图像批判,这样才能使我们逃脱图像解释的力量,特别是人的图像的力量。对教育实践而言,对一个儿童和青少年图像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批判同样适用于教学话语中生成的观念和图像的批判。如果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图像和想象力在儿童教养、教育和社会化过程当中的重要性,那么就要求我们自身从与儿童青少年、与世界、与我们自身的关系当中解放出来。”虽然这是全文的末句,但正是此句让全文升华并与教育紧密相连——图像与想象力相互影响生成形象,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我们在看到其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警惕其背后的权力宰制并反思。而这正是一种呼唤——呼唤着教育学界对“学生图像教育”的重视。
由此了解作者的思路,我们对《人的图像》一书就有了一个更为教育学的视角。事实上,本书虽然名为《人的图像》,但重点并非讨论“什么是图像”,而是“如何使用图像”,而这就涉及到前文反复提及的主题——想象力,它与图像的重要性可以等量齐观。如果说《人的形象与图像化》是呼唤着教育学对“图形教育”关注的号角,那么《人的图像》就是其扩展版及操演手册。
在书中,作者开篇就指出,图像在如今的生活中可谓无处不在,而对它们分析乃至探讨都是有必要的。它不仅仅是艺术学、社会学、传媒学的命题,同样是教育学应当关注的对象。在进入教育学之前,作者首先就图像与想象力做了梳理和挖掘。
全书分为四部分,分别是“图像与想象力”“想象力与想象”“想象力与身体实践”及“模仿与文化习得”。武尔夫教授依据“图像——想象力的作用——想象力下图像的再现——图像的演述——演述中的模仿——作为模仿的文化学习——图像教育的重要性”这一路径,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作为图像可以分为哪些类别,并探究其中的不可见者;而后将隐蔽的作用于图像的力量——想象力提取出并予以阐述。
武尔夫指出“想象力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能量,能将不在场的人、对象抑或事物关系进行表征”,正是通过想象力,我们才能将外部世界转化为图像和表象;继而,武尔夫对想象力展开了论述,首先将其相关研究文献加以综述,并进而上升至社会文化层面,探究其如何形成社会性的认知体系;武尔夫指出,如果“幻想、想象力与想象世界要获得其表演性,那么他们主要是一种力量,一种形成图像的能量。”由此,想象力的能量又将图像推向了权力的舞台,并且通过形成“内在精神图像”指导人类如何观看、学习外部图像,武尔夫认为,“内在精神图像”是历史文化的构建,受到社会仪式的强化,并借助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指出了不同阶层的“内在精神图像”之差,继而综述了民族、性别等对其形成的影响,并点出了内在精神图像的形成机制——模仿,而后将模仿的前提——演述性置于台前。
而演述性则让图像权力更进一层。通过考察游戏、舞蹈、仪式表演及体态语,武尔夫认为这些活动都是图像的演述,通过展示这些图像,它们构建了一个对于现实世界模拟的想象世界,而个体(尤其是孩童)则通过模仿习得其中动作、规则、角色等并进而习得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这些图像不仅仅是肉体规训,更是文化与价值的负载。个体在这些演述性图像中无论是通过模仿,还是观看,都会被其背后的意义所辐射,成为个体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并且再生产为个体图像与集体想象世界中的一部分。
由此,图像的权力彻底彰显——其被凝视、被模仿,在操演中构建了个人与社会。铺垫了图像的权力及其演述性与被模仿性,武尔夫最终落笔教育,指出“模仿性学习是学习的一项重要形式”。而这正是图像教育的精髓之处——个体通过图像的模仿性学习(或凝视、或操演等),从而习得其本身,进而浸入其背后的文化与社会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完成着自身的主体化,同时也将外部结构通过构建“内在精神图像”的机制内化,又完成着自身的社会化。而建立在此之上的“探究性学习”无疑是图像指导下的教育,图像俨然成为了权力的隐形代言者,在不知不觉间完成着教育的使命——而这也正是《人的形象》一文中武尔夫教授所强调的。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首先论述了模仿性学习的内容,包括主体建构、社会行为、实践性知识以及差异的文化(其中将物质文化遗产单独论述),他指出,儿童正是在对图像的模仿与演述之中,通过想象力构建起“内在精神图像”并作为认知与行动的元结构;在此处作者提醒我们的是。家庭中的仪式也是儿童模仿性学习的重要内容;在家庭生活中,孩子会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与想象力所构建的图像与图式共同作用于其心智结构与幸福感体验。图像既形成于家庭生活,又指导着家庭生活的进程,由此可见图像对于青少年儿童成长的影响。
关照到这些角度,武尔夫教授认为:图像、想象力与想象世界的构建在人一生的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的理性认知,更是其探究性学习与情感体验的重要途径。但非常遗憾的是,它们尚未被学校重视,与“感知”一道被“理性”所遮蔽,教育学忽视了图像的力量与教育性,仅仅将其作为艺术教育的一项内容,而未能挖掘其对于儿童与青少年主体建构与社会化的重要性——换言之,对于图像的社会文化教育作用关注严重不足,忽视了“将学生培养为人”的重要教育价值。因而作者疾呼图像教育的必要性。
在尾声中,教授重拾了“图像的力量”这一主题,再次总结回顾了图像与想象力的关系,并总结了全书的重点内容。借助对于全球化的展望,作者进行了福柯式的论述:图像的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与社会文化所交织的“知识型”(尽管原文并未明确提出),进而再次回到了出发点上:世界既然“被把握为一幅图像”,那么“让学生学会如何去把握、去使用它”便是亟待教育者解决的问题。
在此处,教授将本书与其《人的形象》一文进行了呼应:教育学界对于图像教育的关注绝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如何利用”上,更要从权力批判的维度去质询图像。作者指出“想象世界的图像影响着我们如何去对待文化当中的差异性,以及如何与他者交流,这也使我们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并且“世界大环境的巨大变革”必须通过“图像、想象力的创造性学习来完成”,因而“模仿性学习过程就越来越重要”,这也正是武尔夫教授的愿景——让学生在把握图像中“活”起来,让“图像”成为生命建构的积极分子,从而真正的发挥其力量。笔者相信,在国内视觉教育正在被重视的今天,《人》的重要性会不断被学界挖掘,乃至延展,为图像教育乃至视觉教育贡献其力。
值得注意的是,身为欧洲学者,武尔夫教授表现出了对于“西方中心”的自我反省。在行文中,“异质性”与“他者”都是反复论述的主题。作者一有机会便提醒我们,西方文化通过殖民、理性等方式排斥了他者的在场,并且进一步将他者污名化——这一点与弗洛伊德的异域凝视不谋而合。同时,“西方中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概念,更是知识型的霸权,制造岐争并自我稳固。我们须得警惕这种知识霸权及符号暴力的暗中统治。
纵观全书,武尔夫教授将图像与想象力作为中心概念不断推演,结合具体研究论述二者的交织,并落脚教育,阐释图像教育的重要性与相关教育策略,为图像教育指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本书与《人的形象》一文一道,都值得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查阅、精读。
注释
[1]克里斯托弗·武尔夫,陈红燕.人的形象与图像化:不可见的可见性[J].基础教育,2017,14(05):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