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lis.D.(2007)The warring twins: sociology, cultural studies, alterity and sameness,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 20(2):99-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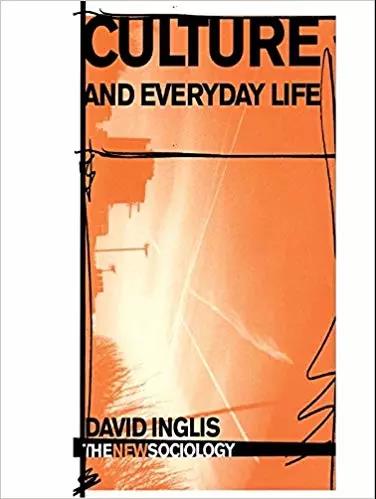
作者简介:David Inglis(大卫·英格利斯)阿伯丁大学社会学教授,专著集中于社会学原理与文化社会学领域,对全球化的文化维度有着特殊的研究兴趣。其2005年所著《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已于2010年翻译成中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学界对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长期存在争论,本篇论文创作于十几年前,试图分别从文化研究工作者与社会学家两种立场就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异同进行分析,指出两者如同易怒的双胞胎,对彼此的敌意强烈彰显着自我意识,因为斗争才逐步增加了各自对自身身份与地位的认同。两者争论不休并非因为其表面的不同,而恰恰是因为两种学科拥有共同的认识论假设,只有通过争论才可以不断巩固和认同各自的学科价值。
文章开始,作者交代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的学科分类不同国家各异,学校教育系统对于学科的划分以及学科定位也均不相同。如在美国的一些文化研究院校多会把文化研究归类为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因其起源更接近于语言和文学,因此一些美国的文化研究更关注文本研究;澳大利亚学校在构建学科边界时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更加混乱,而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实体学院多可能设在技术本科院校,而很少在一些长期由社会学占据的老牌大学出现。因此要更细致描述两者差异需要明确的背景阐述,然因本文篇幅有限,笔者以两者的学科立场,分别以理想典范模式(ideal-typical modes)去描述“自我”(Self)和“他人”(Other)。
首先,作者以文化研究工作者立场从四个方面阐释文化研究的优势:一、开放性与流动性,文化研究强调问题意识而非提供答案,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化研究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了文化的复杂性,尽管其研究存在不明确性,但文化研究学者则认为其是一件好事,是其学科活力的象征;二、学科边界问题,文化研究强调了“新”,打破社会学陈旧的概念规训,同时鼓励多学科参与文化研究,形成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参与的交叉学科领域;三、概念化方法的多样性,基于学科参与的多样性,其研究方法与概念的多样性不言而喻,文化研究领域之所以涵盖如此多的理论是因其学科由伯明翰学派建制正式成立过程至今经历多种挑战的历史发展进程所决定的,至今没有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研究方法与理论,而我们所了解的文化研究概念众多,例如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文学与哲学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文本主义和解释主义人类学、后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四、高度的政治参与,尽管其拥有概念的多样性,但所有的文化研究者都以两方面强调其学科地位的特殊性,首先是文化形式与实践的关系研究,其次是文化形式与权力的关系。
之后,作者从社会学家立场加以,一部分社会学家认为随着所谓的文化转向,社会学被分解为了一系列新的领域,如文化研究、女性研究、城市研究以及媒体研究等。而作为独立领域的文化研究本身则多关注商业与大众文化,追逐文化潮流,并被描述为“装饰社会学”,只注意表面而缺乏对历史和系统的理解,缺乏对社会结构的认知,将社会现实简化成文本这样的研究并不能知道是不是作者主观臆断。
尽管笔者分别以文化研究及社会学立场批判了对方,但其意在探寻其不同背后的相似。并指出学界支持两者交互发展而非分离的主张。作者指出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都是典型的由康德哲学的“社会科学”解释派生而来。康德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是它的本体的一面,那是它的本质,它存在于人类的知觉之外;另一方面是它的现象的一面,那是它在人的知觉中出现的客体。后康德主义尤其是社会科学层面否认了本体的存在,认为世界仅仅是一系列的现象,不同的人群共享不同的文化,而所有的文化都是建构的,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中心信条。
随着“社会与文化理论”的发展,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已经逐渐共享理论与方法,不再像以前一样对立,当代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工作者应当更加关注他们共同的认识论基础,更多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怀疑,谨防被“正统观念”所限制,更不要被传统的学科教条所影响。
这篇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文章,尽管无法涵盖文化研究与社会学发展的全貌,但其以二元论的“争论”方式探讨两种学科存在问题,以辩论的方式梳理两者的发展历程呈现两种学科的异同,其目的并非为读者提供正确答案,而是鼓励读者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与对话厘清混杂的概念,承认其认识论上的同源属性,不过多执着于学科边界及所谓的特性。最后作者引用布迪厄提出的”misrecogonized”诠释对于“真相”的执着,无论作为社会学还是文化研究,两者都无法代表真相,当执着越深,误解就会越深,误以为自己代表了世界的真理,而最终不过是一场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