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罗伯特•埃默森雷切尔•弗雷兹,琳达•肖著.符欲,何珉译. 如何做田野笔记[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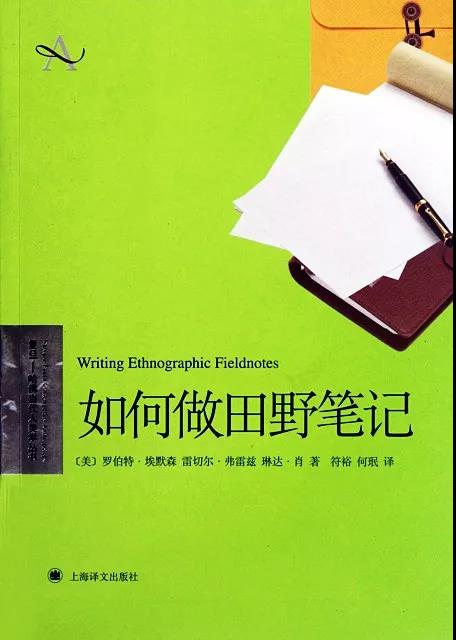
“复旦-哈佛人类学丛书”自2007年起先后出版10册人类学研究著作,向中国读者展示了国际上人类学理论、研究方法、实证发现和应用实践方面的最新成果。尽管很多研究已经过二十余年,这些著作所具有的研究代表性依然影响显著。本次推荐2012年该系列出版的《如何做田野笔记》一书,由美国多位人类学教授联合撰写而成,对深入田野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来讲是一本实践性极强的工具书。
尽管本书并没有直接从理论层面探讨田野笔记工作方法的研究范式,但其却通过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数据、资料的态度及可能发生的实际情境进行阐释,时刻强调田野数据收集过程中的解释性特性。此书以田野笔记从收集、整理到编码的各个环节步骤依序组成章节,通过大量田野笔记撰写案例分析如何更全面快速地梳理研究者所需要的田野研究信息。此书可以当作工具书使用,在田野调查的任何环节都可以随时翻阅以寻找到一些必要的技巧,而于读者最有益的则是进一步明确了田野记录对于研究的作用。尤其是对扎根理论与田野研究的对比分析,阐释了田野研究的价值主张:
扎根理论更加看重的是自己发展出而不是去验证已有的命题。这一理论认为如果研究者能够减少对已有理论的接受和依附,就更有机会从自己的数据中“发现”原创理论。研究者通过不断分析、比较收集到的数据,可以提出、完善并扩展出最切合数据的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田野工作者从细致而系统的编码入手,从而提出分析性概念。然后,他们将通过撰写理论性备忘来进一步详细说明、拓展并整合所形成的概念。在信奉扎根理论的研究者眼中,分析过程是一种明确的甚至自动的研究活动。当信奉者强调从田野笔记或是其他定性数据中“发现”了理论时,他们默认田野笔记中的数据是毫无瑕疵的,可以作为分析的起点;他们的言外之意是任何研究者都可以撇开田野笔记作者的分析过程和理论取向来分析这些笔记。相反,我们认为数据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分析过程存在于研究的各个阶段——存在于研究者观察的时候,将观察所得记录下来的时候,进行分析性编码的时候,直至最终形成鲜明的理论观点的时候。从这一观点看,分析过程本身既是归纳性的也是演绎性的,这就像一个人同时制谜又解谜或是一个木匠在改变门的形状之后相应改变门框的形状一样。
的确,田野研究本身最困难的部分是研究者与自身的和解。田野研究中研究者本身事实上是最重要的研究工具,又是最无法被外界控制的因素。人的主观性是隐匿的,在多数时候可能研究者自身都无法意识到潜意识中的预设、偏见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而当全然置身于田野之中时,研究者所接触到的声音又是庞杂的喧嚣,而非线性的因果关系推演,看似简单的研究问题在置身田野之中后,变得多元复杂,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口中都会得到不同的诠释。切身投入田野的研究者,恐怕都曾有过对于“真实”的质疑。
通常,田野研究容易纠结于现实的复杂以及写作的局限,无法将生活的全貌以文字的方式全息呈现,片段的信息组成完整论述的过程中需要作者主观参与进行重组及删节,被过滤掉的却依然是生活的现实,而因为如此过程,接受到的便不再是“真实”。因为执着于“真实”,所以惶惶然不敢下笔。然而,此书在教授操作方法的同时为研究者做了相关的心理建设:田野工作者应该接受知识生成过程中的流动性和局限性,接受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承认田野笔记是在关系互动中形成的具有主观参与的信息;接受信息在一定时间、空间层面的局限性,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都包含掩饰和伪装的成分,即信息可能存在的欺骗性;接受系统的复杂性,并通过复杂系统与研究者的共同作用,创造出的新理论。
破除对于“真实”的执着,接受知识创造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是田野研究工作者应有的认知。无时不在的反思与自省是田野工作者自我成长的必需。不论田野笔记究竟是以何种形式出现,不论田野笔记是否是研究的中心,撰写田野笔记本身不仅仅是记录田野所发生的事情,更是关注在田野中的自己是否以沉浸的方式参与,又以理性的方式出离,尊重现实又开放地接受信息可能存在的偏差。
此书为为田野工作者提供了便捷的操作说明,而真正获得同理心、出离心、平常心的研究心态,则需要长久的积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砥砺前行,磨砺心智亦是一位田野工作者一生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