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雅克•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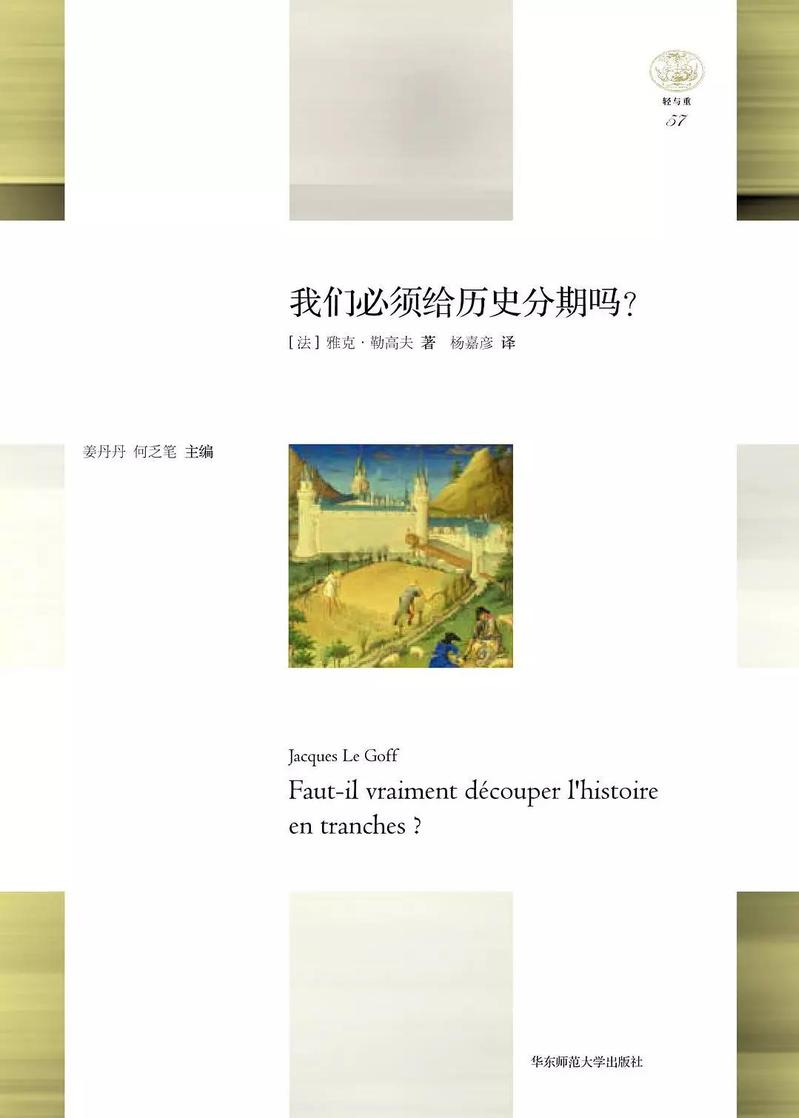
“历史学家从来不能摆脱历史时间的问题,时间粘着他的思想,一如泥土粘着园丁的铁铲。”
——费尔迪南·布罗代尔
“年鉴学派在其全部的历史中,始终引人瞩目地从未染上过对基于科学与技术之上的那种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的信念,也未曾染上称其为大多数科学核心的那种现代化信念。反之,他们是专心致力于前近代的世界。”[1]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伊格尔斯将第五章留给了年鉴学派,称赞其冲破线性时间思维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对于近代的研究关注不足。然而对于年鉴学派而言,前近代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在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关照下,身为年鉴学派第三代“双子星”[2]之一的勒高夫便提出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命题。他认为,中世纪一直持续到了十八世纪——这是本书的核心观点,也是作者一生思想的浓缩之笔。
与兰克史学等传统史学派不同,年鉴学派一直致力于“总体史”的建设,而非单纯的政治史,尤其关注日常生活史。并且,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段”这一概念。所谓长时段,即是指结构,包括地理、心理、文化、社会、经济等种种结构;而年鉴学派认为,事件与趋势都是一时的,恰恰是这些结构才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长期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年鉴学派(特别是第二代)在时间表述中,往往避免使用“古代-中世纪-近代”的话语,而会转向“世纪”等较为中性的概念。作为一场运动而发端的年鉴学派,也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史学派产生冲突。
师承布罗代尔,勒高夫主动为学派辩护,在其《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3]中,集中回答了关于时间与中世纪的问题。
全书共分八章,勒高夫从“旧的历史分期”开始,将“中世纪的较晚出现”“历史,教学,时期”“文艺复兴的诞生”三部分进行梳理,转而评述学界关于“文艺复兴”与“中世纪黑暗”的研究思潮,最终落笔“历史分期与全球化”进行总结展望。中文版只有短短133页,却弥足珍贵。
勒高夫开篇便对“旧的历史分期”做了回顾。他论述了犹太人、圣奥古斯丁、伏尔泰等人的历史分期法,并且指出伏尔泰的分期“将其他时代置于阴影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中世纪。
在第二章中,作者溯源了“中世纪”这一概念的演变,论述了中世纪这一提法是如何从彼特拉克发端,经由塞拉里乌斯定义,并由欧金尼奥·加林赋予贬义;直至19世纪方才逐渐重新被重视。勒氏本人则认为,中世纪并非是“黑暗”二字所能遮蔽的,且文艺复兴也并非一个特殊时期,而是镶嵌在中世纪之中。循着概念这条路径,勒高夫在第三章追溯了历史分期对整个研究与教学的影响:他发现,历史学是在18—19世纪才真正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教学科目”,并且欧洲国家才逐步开设了大学讲席。而为了能够更好的教授历史,系统性的将历史分期是必不可少的:这也造成了古代——黑暗的中世纪——光明的文艺复兴以及之后的划分法。而这一划分恰恰是勒高夫想要商榷的对象。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勒高夫梳理了学者们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包括米什莱、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热情赞美;克利斯特勒、加林对意大利中心性及文艺复兴的“新人”的能量的肯定;潘诺夫斯基以及德吕莫对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与技术的探索等;紧接着,勒氏指出:正是在文艺复兴发端,启蒙运动爆发之后,人们对于中世纪愈发贬斥,认为它割裂了古希腊的传统,并且使得基督教一手遮天;而这也导致了后世者对文艺复兴特殊性的过分拔高及对中世纪不公正的审视。
在此,作者为中世纪的这些污名洗冤:首先,中世纪并未忽略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并且还时常在使用及延续;其次,中世纪实现了语言的极大进步——拉丁语在基督教地区广泛传播;再次,基督教确立了形式理性与经院哲学,为理性启蒙与世俗哲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中世纪也已经孕育了“现代性”这一概念的雏形,并经吉尔松、格鲁特、贝尔纳等神学学者推演;最后,中世纪在艺术方面也成果斐然,包括绘画、建筑、音乐、文学等艺术样式都已经含有人们对“美”的追求以及世俗化的前奏。经过此番论述,作者认为将文艺复兴看做是对于中世纪的断裂与弃绝是不妥当的。
接着,在第七章中,勒高夫指出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内在连续:在生产层面,农业生产仍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形式;在经济因素层面,两个时期的经济思想一脉相承;在饮食层面,中世纪兴起的面包、海鲜、配料等一直是文艺复兴时期餐桌的常客;在金属应用、服装设计、军事技术等层面,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兴及发展趋势同样是承继中世纪的;同时,作者也回应了1492年[4]作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分期的传统依据,他认为:地理大发现、财富的运输与现代性的提出并没有让欧洲立即进入资本主义,而是依旧在中世纪的惯习中发展着;同时,现代诸多的活动,如金融、宗教改革等也在中世纪已有雏形。综上,作者认为文艺复兴并非是中世纪的反叛,相反,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某种延续,即中世纪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同样的,学界强加给中世纪“黑暗”、“落后”的标签也是不可全盘接纳的片面之词。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于历史的分期就是无效的呢?在最后一章中,作者也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长时段与历史分期是并行不悖的,将连续性与断裂化结合才能够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历史。换言之,结构、趋势与事件必须共同把握方能接近真相。同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也不应当将统一化混淆其中。全球化有两个阶段:交流、融合;而直到今天,人类“还只是处于第一个阶段”,而后一个阶段的完成也依赖于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纵观全书,勒高夫首先论述并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分期及其影响,认为将中世纪以黑暗的年代盖棺定论是有失公平的;其次,勒氏综述了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并且指出了学者们对于文艺复兴反叛性的夸大,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仍然是中世纪的延续,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一次发展而非反叛,事实上的中世纪包含了文艺复兴直至18世纪中期。在厘清了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关系,并为中世纪正名后,作者仍然肯定了历史分期的价值,并强调要将其与长时段相结合,全方位的看待历史——事实上,最终勒氏回到了“总体史”的学派视角。
对于读者而言,勒高夫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独特的分析视角都是值得揣摩的。史料的引用,对其他学者的文献评述无疑是个人分析的基底;而不盲从于“黑暗的中世纪”这一论断,发现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及其对后世的滋养,则让本书闪现其光芒——大胆论述,精心求证;无论是否从事历史学研究,这都是值得研究者们应有的态度。
而勒氏也提醒我们:新事物的树立,往往伴随着对旧事物的打破,它急切的需要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而旧事物便是其攻击以自立的优质靶子。这犹如弑父的子女一般,宣告自己将会带来美好的光明,而黑暗属于“罪父”——然而,血脉怎会轻易断裂?“革命的第二天”永远都有过去之影[5],弑父的宙斯依然被其祖辈乌拉诺斯的警告所笼罩。而这警告也这无疑给了我们警示,特别是对于学界而言,对新事物固然要以包容、开放的心去对待;然而同时也要冷静思考与分析——新与旧之间,真的是单线性发展、彼此截然对立的吗?过去真的“一去不复返”吗?以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为例,这本身就是需要反思的问题。巧合的是,被年鉴学派当年所遮蔽的“王之二身”的研究[6]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个问题,用施密特的话来说,“一切当代政治不过是神学的转移”。[7]
总之,勒高夫承袭本学派的视角,探索老师布罗代尔所开辟的道路,集成了这本《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短短百余页,却从研究态度、方法、视角、分析等各个层面给研究者们以启发。无论是否从事历史研究,笔者认为,勒高夫乃至于整个年鉴学派的研究成果,都是学界宝贵的材料。尤其是在年鉴学派自我重新定位的今日[8],我们更可以其反照自身,在研究反思中不断前进。
注释:
[1][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2]“双子星”通常指勒高夫与勒华拉杜里,二人都是布罗代尔的高足。
[3]本书法文版完成于2013年,出版于2014年,作者也在该年逝世。
[4]传统上,一般将1492年作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分界点,这一年哥伦布出航,正式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具体参见:[英]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1492:世界的开端》[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
[5][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6][德]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7][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神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8]年鉴学派学者马克·费罗曾经公开表示:年鉴不是一个学派,而更倾向于一场运动。具体请参见:[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