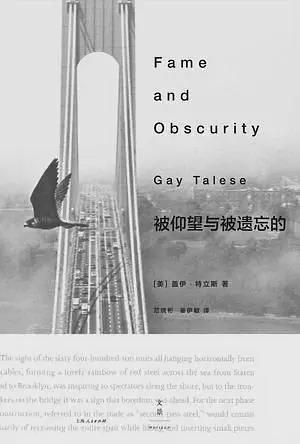[美]盖伊·特立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M],范晓彬、姜伊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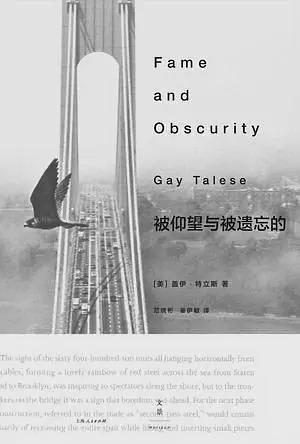
“我们既是事实的提供者,更是故事的讲述者。”
——布隆代尔[1]
本雅明曾将新闻业看作是“讲故事的陌生人”——“与故事的丰富性相比,新闻消息的价值如昙花一现,荡然无存。”[2]事实上,新闻界长期有着文学手法能否进入其间的争论。而兴起于美国19世纪末的带有文学性质新闻报道可谓部分应承了本雅明的观点。1973年,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出版的《新新闻主义及选集》正式将文学与新闻的结合予以正名,也将“新新闻主义”推向前台。
“新新闻主义”是“一种新闻报道形式。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主张记者可以在新闻报道中描述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3]新新闻主义将文学以及想象力引入了新闻报道中,以旁观者的视角对对象进行观察并试图将之全面描绘与洞察。本书的作者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就是此间高手。
特立斯工作作风老派而“衣冠楚楚”,据本人称“从不使用录音笔,而是坚持传统的纸笔记录”。然而,与此相对,他所探索的题材却屡屡“犯禁”:从《窥视者》中对旅店房间的非法监视,到《邻人之妻》中对“乱性”的探究,再到《王国与权力》[4]中对曾就职的《纽约时报》发展史的深入挖掘等等。特立斯将文学与新闻报道相融,坚守非虚构写作的底线,同时让故事“楚楚动人”。
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这样打量城市”,在《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中,纽约不仅是人们认知中的繁华、发达与忙碌的表征;更是哥谭[5]市民饮食、生死、行走、生活等片段的真实接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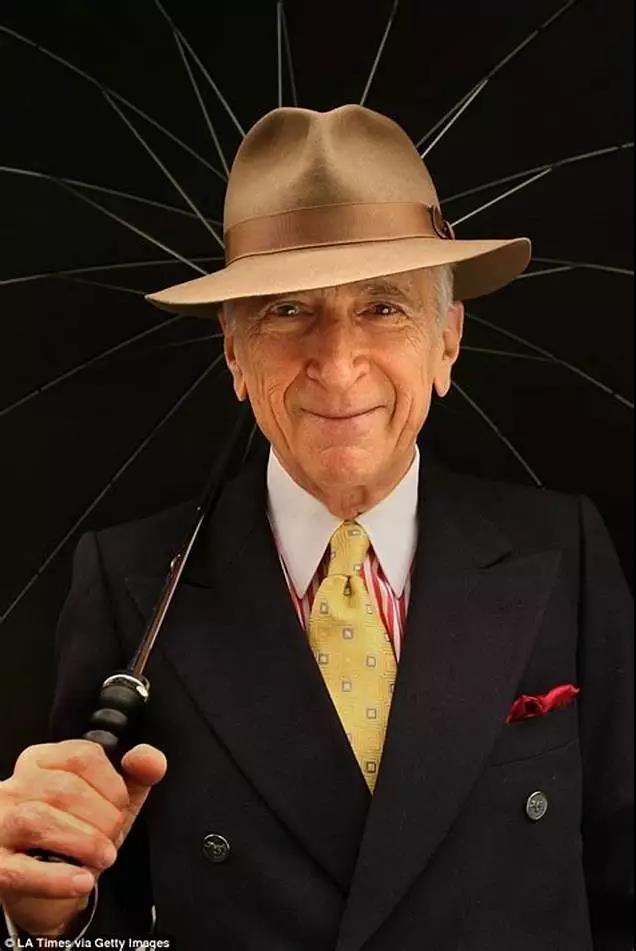
盖伊·特立斯
《被仰望与被遗忘的》(Fame and Obscurity)分为三部分:《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大桥》《走向深处》,分别从三个视角揭示了上世纪60年代纽约的日常生活。三部分各自由若干篇特稿组成,将新新闻主义的特点——文学性贯穿其间。
第一部分《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也的确名副其实:单看“被忽视”、“匿名者”“个性”“奇特职业”“被遗忘”这五个标题便可见一斑。特立斯向我们展示了纽约市民那似乎为人熟知但又不为人知的生活图景:有底层劳动者的付出,有残障人士的辛苦坚持,有乘务员对待陌生人的日常,有无家可归者的流浪,有逝者家属的悲哀,有越轨者的暗夜,有商人的精明算计,有白领的媚上讨好,有巫术师的魔法占卜,有鸽子、猫、雕塑不语中的鉴证……深入街角,特立斯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个真实的姓名与事件。在这里,纽约的日常是在“每天46万加仑啤酒、350万磅肉的消耗”“15万人带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每天250人死去,460人出生”中发生的,被“无名者的集合”所贡献着。这些无名者就是“被遗忘者”,也可以称为“沉默的多数”。然而正是这些“沉默的多数”,却让特立斯用“惊奇”与“敬畏”形容所见——“被遗忘者”的生活虽不见经传,却同样精彩纷呈;“自以为熟知往往无知”(黑格尔的训诫此刻降临)——不仅是纽约,任何一座城市都是如此,在“熟知”中隐藏着数不清的待猎奇之物。而这一篇篇特稿在猎奇的同时,也重绘着普通人的生活。
如果说“沉默的多数”作为“被遗忘者”是一个平面意义上的遮蔽,那么“劳动者”这一“被遗忘的群体”就是大叙事的垂直掩盖——特立斯将目光移向大桥,花了三年时间深入韦拉扎诺海峡大桥[6]的周边人群——包括修桥者,周边居民与管理人等,并且见证了他们关于这座桥的生活。在这里,特立斯将这些被遮蔽的人与事一一展现:包括被修桥影响的小商人与政府部门的对峙、修桥者工作环境的恶劣与随时替代的危机、修桥者与监工的斗智斗勇、周边居民为了修桥所导致的环境破坏的反抗、修桥中发生的种种故事与事故以及与工人们的对谈等等。特立斯将整座大桥的修建经过记录于纸面,详细的展示了修桥是如何影响与其相关之人的生活。在特立斯的特稿中,修桥不再是一项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而是修桥工、周边居民等人生活的接合——尤其是修桥工,面对着恶劣的环境,承载着繁重的工作,承担着被替换与无工可做的风险,更要做好随时发生意外的准备:在这一章中,题为“桥上之死”的特稿专门讲述了一名年轻的修桥工如何因为意外而去世。讽刺的是,鲜活的生死现场最后却被官员做成了可以表彰的“低伤亡率”——只发生了三起死亡事件!未给予置评的特立斯此时“无声胜有声”——生命的温度就这样被数据所遮蔽。
在对“无名者——劳动者”这些“被遗忘的群体”描绘之后,特立斯将“名人”这一“被仰望的”群体纳入了哥谭叙事的版图。在第三章《走向深处》中,他追踪了歌手弗兰克·辛纳屈[7],乔·迪马乔[8],弗洛伊德·帕特森[9],演员彼得·奥图尔[10]等名人的生活轨迹。与一般记者的视角与做法不同,特立斯对于一些名人连访谈都未曾有过;然而他并不拘泥于此道,在收集其他资料的同时,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前往这些名人出没的场合屡次追踪,逐步刻画其形象——他们不仅仅是承载着风光与记忆的符号,更是有血有肉的人;面对情路波折、职场竞争、公众舆论、意外与诱惑等种种,这些头戴光环者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必须消化更多的孤独。特立斯深入他们的光环背后,将台前幕后都展示笔间:不止有花团锦簇、谈笑风生的高光(highlight)时刻;还有品尝着孤寂、被背叛、被压力与对手击败的暗流时段;更有其作为平凡人而生活的点滴。特立斯将这些名人的生活图像串联成了图景,让读者在阅读间看到一个个接近真实的名人,原本应当是“被仰望的”名人。
行文间,特立斯保持了“中立”笔法:叙事为主,很少置评。但其对人性的关怀却满溢纸上:
“乞丐死后,他们的尸体被运到城市停尸所,等待认领。如果几周之后无人认领的话,就被拉去埋葬。不是被葬在他们所选择的城市里,而是葬在这个遥远的小岛上。这样,活着的人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人的坟墓,也就不会产生什么不快的想法。”
“他们(修桥者)把所有地方都连接起来,而他们的生活却永远是那样支离破碎。”
“那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注视着他(指弗兰克·辛纳屈)。他用左眼余光看到了她。每天这种情况都发生,他知道女孩一定在想,这个人很像弗兰克·辛纳屈。但,是他吗?”
特立斯的温度与态度在其间浮现——对于平面中的“被遗忘者”,他给予深情的凝视,赞颂着他们的生活——在行动中为纽约的光华奠基;而对于被大叙事遮蔽的“被遗忘者”,他不仅给予他们同情与钦佩,也将对那些漠视生命者的控诉的意指藏于字里行间——这层意指并不像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难读;对于那些“被仰望者”,特立斯“游戏”着让他们走下神坛——“被仰望”并不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被仰望者”一旦祛除了名人的光环,就犹如赤裸生命一般可以被肆意践踏,“高处不胜寒”,荣誉的身份同时也是枷锁;而在特立斯这里,描绘“被仰望者”的生活成为了祛魅的游戏,当我们逐步近观“被仰望的”这一群体,真正意义上的“人”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也越发能够让他们“平安着陆”。
纵观本书,特立斯用“无名者——被遮蔽者——名人”这三个元素拼接了一个“新新闻主义”者的纽约。他细致的描绘了无名者的日常生活,田野般的与劳动者接触,又锲而不舍的追踪着名人的点滴。这些特稿不仅展示了纽约市民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也将一个“活”的纽约接合起来——纽约不仅仅是“时尚之都”“金融中心”标签下的宏大叙事与奇迹,也是千万人默默行走、呼吸、耕耘下的日常生活空间,无论是“被仰望者”还是“被遗忘者”都值得尊重与铭记。给“被遗忘者”关注,让“被仰望者”喘息——这是特立斯的温度,也是纽约的温度,更应当是研究者的温度。
“非虚构写作”是新闻行业的基本功课,本书堪称特立斯的教材之作。其特稿的行文风格吸引了诸多新闻工作者效仿——千禧年以来,中国诸多新闻特稿都带有特立斯式的写作痕迹。而非虚构写作不仅仅是新闻工作者的基础课程。在叙事研究不断推进的当下,它更应当是相关研究者的必修功课——能否讲好故事,直接决定着叙事研究的成败。“微观叙事”有着与“元叙事”一样宏大甚至更为巨大的能量——在真正的“微观叙事”中,生命力与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而这一“真”不仅让故事可信,更能让读者浸润,使得研究能够立足并稳步前行。
特立斯曾言不愿写作“第二天就被扔进垃圾桶的新闻”,而文学融入的“新新闻主义”也并未引发新闻的“真实危机”——相反,它让新闻更有深度、更切人心、也更为长久。在“新新闻主义”思潮的背后,不仅发生着新闻写作的风格演变,更折射着人文学科的视角变革——深入微观现场、深刻描绘日常生活、讲好日常生活中的故事。而这正是特立斯努力的方向,也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注释:
[1][美]威廉·E·布隆代尔,《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德]瓦尔特·本雅明,单向街[M],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3]徐叶.新新闻主义——新闻客观性的扩充[J].当代传播, 2008 (3) .
[4]其中,《窥视者》尚未有中文版,而其余两本已经有中文版面世。
[5]哥谭(GOTHAM)最初被用于指代城市人;1807年,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用“哥谭”代指纽约,此后这一别称风行开来。
[6]韦拉扎诺海峡大桥位于纽约市,修建于19世纪60年代,是沟通斯塔滕岛与布鲁克林的重要桥梁。
[7]一译法兰克·辛纳屈(Francis Albert Sinatra)(1915-1998),美国著名歌手。
[8]一译保罗·约瑟夫(JosephPaulDimaggio)(1914-1999),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
[9]Fraud patson(1935-2006),美国拳击手,曾获得拳王。
[10]Peter Seamus Lorcan O'Toole(1932-2013),爱尔兰演员,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