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洞穴
读《表征的重负》

【美】约翰·塔格
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
周韵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294186/
“蕴涵于事物表面的问题, 而且只有蕴涵于事物表面的问题, 才是事物的核心。”
——列奥·施特劳斯[1]
[1] 列奥·施特劳斯.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M].申彤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2003.6.

摄影作品《只差两秒钟》(1976)
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曾斥责二流视觉艺术家将顶点发生的瞬间记录下来,从而让观者丧失想象力。相对的,他慷慨地赋予了诗歌这种特权[1]:
既然在永远变化的自然中,艺术家只能选用某一顷刻,特别是画家还只能从某一角度来运用这一顷刻;既然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不是让人一看了事,还要让人玩索,而且长期地反复玩索;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选择上述某一顷刻以及观察它的某一个角度,就要看它能否产生最大效果了。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想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我们愈看下去,就一定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我们在它里面愈能想出更多的东西来,也就一定愈相信自己看到了这些东西。在一种激情的整个过程里,最不能显出这种好处的莫过于它的顶点。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因为想象跳不出感官印象,就只能在这个印象下面设想一些较软弱的形象,对于这些形象,表情已达到了看得见的极限,这就给想象划了界限,使它不能向上超越一步。
摄影则轻而易举的逾越了这条红线——与其说是逾越,毋宁说是无视。对于摄影而言,记录似乎是它最原始也最为忠实的功用:至少我们可以对这一张照片说:事件真实发生过(即便它是虚假的),每一瞬间都是真实性的顶点。正如巴特(Roland Bart)所言“每一张照片与其指称对象一样自然”[2]。
然而“摄影无罪,真实其罪”,“眼见为实”的信念使得摄影负载其不应负载之物——它能够充当法庭诉讼的证据,可以作为海誓山盟的见证,亦可成为白云苍狗的截存。于是,摄影复杂了起来:它追溯在场,还原在场并逐渐僭越在场——甚至它被宣称是唯一的在场。我们由此掉入影像的洞穴,于是我们不得不尝试走出来,摸索这洞穴之外的世界。而《表征的重负》一书,或许可以作为我们探路的手杖。
[1] [德]莱辛. 拉奥孔[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8-19.
[2] [法]罗兰·巴特. 明室:摄影扎记[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6.
1.
>>>现代生活的画家<<<
摄影与真实
摄影如何被发明?通常意义上,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被尊为摄影的先驱——利用镀有碘化银的钢板在暗箱里曝光,然后以水银蒸汽显影,再以普通食盐定影[1]。虽然保存与曝光都很短暂,然而当真实点被摄影固定下的那一刻,它就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视觉上它比任何大师、匠人的绘画都能够忠实而客观的反应现实,可谓一名称职的、描绘现代生活的画家[2]。

达盖尔作品《巴黎街景》(1838)
作为想要探寻画家身影的学者,约翰·塔格编著了该本《表征的重负》。该书是其摄影理论文集,共收录七章内容,其编排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被一些学者列为摄影领域的基本读物。
言归正传,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可以详细了解摄影的早期发展:事实上,早期摄影曾被保守主义者抵制,并且技术上面临重重困难——但公众高涨的热情很快就冲破了这些阻碍:
“(商业的和殖民地的竞争对手表示)只有神圣的艺术家,为灵感所激发,才允许在庄严时刻,在天赋的感召下,斗胆复制神·人的肖像,但从不用机械辅助手段。”
“照片上的银色表面非常脆弱,必须像保护珠宝一样放在盒子里,除了细微点彩,也不能做其他装饰。”
“在十年,美国就有了两千多位银版摄影师,且整个国家每年花在找乡村上的费用为800-1200万美元,占摄影生产的95%。”
时间推移,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与人们对科学的神往下,技术的进步必然是飞速的——从早期笨重的相机到莱卡的诞生,战后电眼相机发展到今日数码相机的普及都使得我们可感的世界越来越清晰而有力,而摄影也逐渐为大众所享受。在照片开始大规模冲洗变得唾手可得之时,它也就从神坛上走下,成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笔下“机械复制时代的作品”:
“1880年代,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持相机出现在市场上,包括‘侦探相机’以及携带多种感光版的相机,不用重装就可以多次曝光,至少12次以上的曝光。”
“人们不再去专业肖像画师那里了,现在无需培训或技巧就可以自己拍照,把这些亲密的、非正式的或者构图糟糕的照片收藏在家庭影集里。”
“照片变得如此普遍,不再引人瞩目。它们是一时的兴趣之物,没有任何剩余价值,消费后即丢弃。这就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图像的‘崇拜’价值被有效地摧毁了。”

上海老相机制造博物馆
灵韵(aura)消失的同时,以肖像画为代表的照片则开始在世俗生活中崭露头角。这些照片装点着资产阶级家庭的空间,同样在社会中弥散并无可逃避,处处都有它的身影。
由此,图像不再是一种特权,一种令人心驰神往趋之若鹜的存在。反而成为了一种治理权力的手段。进入近代以来,图像与治理权力媾和,延伸自体作为档案的一部分存在着,记录并监视着特定时空中的个体生命。这位现代生活的画家的技法越是高潮,监视也就越娴熟,描绘的真实也越发不可反抗,也就越发迫人规训。
[1] 刘周重托. 浅论西方绘画与摄影的关系[D].南京艺术学院,2018:17.
[2] 在摄影出现之后,西方艺术也发生了转向,由纪实主义逐渐脱离出来。
2.
>>>生产之镜<<<
作为档案的摄影
提到档案(archive)一词,我们本能地就会想起铁皮柜与文件袋。它似乎属于中性,历史,过去这些词汇,永远静静躺在那里等待有心人查阅。然而,伯格森(Henri Bergson)提醒我们:外在刻度只是时间存在的外向度,而内在的、非空间化的时间正是一种绵延(durée),是连续的且不同质的[1]——这意味着,档案已经悄悄“侵入”了我们的意识中,它以貌似中立的姿态塑造着我们的过去,并在绵延之河中建构着我们的现在。换言之,正如档案学家特里·库克(Terry Cook)所指出的,“记忆就像历史一样根植在档案之中, 没有档案, 记忆就会摇摇欲坠、对成就的认知就会消退、对过去的骄傲就会消散。档案挽救了这些损失, 档案包含了已经消失的证据, 这在现代社会尤为贴切……”[2]。
因此,我们不得不进行追问——档案的权力在谁手中?谁书写档案?又如何书写档案?档案有着什么样的权力?这些问题使我们将目光投回一位老朋友身上——在五十年前就对此进行思考的福柯(Foucault)。
在《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一书中,福柯将档案的边界扩大了——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来的东西的规律, 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的系统。”[3] 换言之,档案是“活”的,它是话语乃至话语体系,是知识与真理。于是,档案就不再是那些冷冰冰而安静躺下的文件,它瞬间弥散在生活中。档案生发于过去,像毛细血管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中,支配着我们现在的话语,牵制着我们现在的行动,引领着我们的未来。
福柯进一步指出,档案是“通过片段、区域或层次呈现出来, 也就是在权力作用下, 有选择的留存下来的。这种有选择留存下来的档案, 目的之一即在于控制社会记忆”[4]。控制社会记忆就意味着控制了过去,掌握过去就拥有了现在,而“谁拥有现在,谁就拥有未来”[5]。事实上,简单举例便可理解这一点——我们每个人自参加社会活动起都会有档案存世(此处档案是有形的),档案中的每一份文件,每一条记录都决定着制度筛选的结果及他人凝视。有犯罪记录(过去)的人(现在)在出狱生活后(未来)常常会四处碰壁,而有功之人则处处受到重视与对待——即便拿到档案的人事单位并不与其相识。
于是,档案作为文字就僭越了它本身的记录性,成为了权力的载体。而当国家权力涉及其中时,内在运作就更为复杂。一如德里达(Derrida)所言“必须根据拓扑法理学、根据执政官住所的规模去做,必须依据事实上是家长制的档案保存者的职能去做,无此,就不可能有档案的出现或发挥作用。去保护自身,被保护,或隐藏自身。执政官的职能,不仅仅是单一的属于拓扑法理学性质的工作。它不仅要求档案存放在某一地方,存在稳定物质载体上,使之具有合法阐释的权威。执政官的权力,也必须将整齐划一、鉴别、分类的功能与我们所说的置放相匹配。”[6] 这就意味着档案在国家权力中的作用更为精细而分化[7]。

档案室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初步想象摄影成为档案之后其权力的升级加码了:文字档案尚能辖制个体,而摄影这一“真实的记录”就使得个体更加无可逃遁。
让我们回到本书,看看约翰·塔格(John Tagg)由档案出发,在2-6章如何探寻了国家与社会权力下摄影作为档案存在的种种表征:
约翰首先论述了“摄影档案与国家发展”: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在秩序重建方面的作用无比重要,为此就需要培养公民的社会服从意识——这意味着战后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逐渐发展起来。而摄影成为这一治理术中的重要一员。它发挥着观看、记录、监控等权力,将现实(并不能够说是真实)呈现在监督者面前。
“解决这个问题(推进工业化与促进社会服从)的办法是,利用日益壮大的医疗、教育、卫生、工程等部门,包括收归的旧有体制和开始接管的私人和慈善机构,扩大干预工人阶级在工作场所以外的日常生活。”
“和国家一样,照相机从来不是中立的。它所生产的表征是高度符码化的,它所运用的权力也从来不是它自己的。”
“一旦摄像师在拘留所、监狱、救助站、医院、精神病院、学校等地准备照相,使用的每个方法都是无言权力的痕迹。”
于是,约翰开始探究摄影这一“毛细血管”:首先,他瞄准了19世纪司法领域内作为证据的摄影。约翰认为,警察出现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保护财富的现实需求,而摄影术恰是满足这一需求的重要手段——警察通过摄影来确定公民身份,并将各类照片与视频作为法庭记录与证据。这一手法被工厂、医院、学校、军队等场域纷纷采用,人们普遍认为“摄影的光学和化学工艺被认定是一种科学利用的‘自然的’机制”,通过摄影可以毫不费力的实现对个体的追踪。摄影俨然成为了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的监视塔,规训这个体肉体的驯顺,某种意义上讲,它与肉体直接发生了暧昧而统治的意味[8]。
“照片作为法庭证据的生产现在是标准实践:用照片辅助交通控制和交通案件的起诉:记录违章驾驶的证据,包括移动警务巡逻车……”
“在戴蒙德医生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精神病院院长的摄影实验中,存在福柯所描述的种种复杂关联:越发细致的观察和越发微妙的控制并存;越发完善的体制秩序和越发封闭的话语并存;越发被动的驯服和越发支配性的仁慈凝视并存。”
“基于知识、控制、功用等重要的三维统一,新的权力意志找到了新的隐喻:不惹眼的小牢笼般的照片帧数。”
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主体在一系列的摄影技术下被生产了出来:无论我们用怎样的名义拍摄,我们事实上都是在将“对象化与主观化”进行延伸,由此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摄影即谋杀”似乎不无道理。约翰进一步将福柯“真理政体”的概念拉了过来,并提出如下问题:
“摄影话语是如何与我们社会所庇护并赋予真理作用的那些特权话语相联系的?用以区分真假的社会构型的运作机制或规则是什么呢?他们如何对摄影产生影响?可用于获得真理的技巧和程序是什么?它们在摄影技巧和程序中又是什么特殊形式?这一真理是如何流通和消费的?它是通过什么途径和体制运作的?”[9]
约翰认为,现实主义是这一真理流通的范式。他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固定性,“能指在其中被等同于先于其存在的所指。”换言之,能指彻底成为所指的指路标;这就意味着摄影这一能指就透明地是其所指,二者构成互文,因而乍看之下摄影=人的公式完全成立。而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摄影堂而皇之进入档案之中,以其“自然真实”进一步加持了档案的权威。
然而,约翰以为这不过是现实主义构建的幻觉,它排斥了历史的表意过程,只将表面的意义采纳并宣布为唯一答案,并以此对社会进行治理。作者在这里寄希望于先锋艺术家来完成拆解工作。
接着,约翰又考察了作为法律财产的照片:同样的,约翰指出资产阶级的法律是与物体系挂钩的,它将人视为生产资本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本身也是被生产出来的。进一步说,私有财产的保护是资产阶级法律的核心。然而,摄影成为了这一逻辑的例外,正如作者所言:
“如果现实总是属于‘某人’,而其摄影是构建在负片上的,那么有人就会问:允许有关现实之所有权的话语的司法条件是什么?此处所指的现实‘总是已经’具有财产特征。摄影师对属于大家的东西——公共领域的街道、河流、辖地水源——的复制,如何把公共财产重新挪用为摄影师的财产呢?摄影师如何才能变成现实之复制照片的拥有者呢?”
起初,法律是并不同意照片成为摄影师私有财产的——因为法学家们认为摄影中并不存在个体的创造,而仅仅是光学的应用。直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使得摄影成为产业,法律才宣布给予照片以财产的身份加以保护。而这其中的逻辑还是资本主义的——成为产业化的摄影完成了从生产、交换、消费的一整个步骤,摄影者仅仅是链条上的一环,真正的生产者毫无疑问是资本,资本主义的法律自然需要为它正名。于是,法律也成为了摄影现实主义阐释的背书。
在资本主义档案与法律对摄影的收编过程中,工人阶级也出现在了摄影中。但约翰并不欲像伯格(Peter Berger)那样强调照片的史料价值[10];甚至约翰指出它是误导性的,需要厘清其背后的历史背景。这里,约翰对利兹(Leeds)[11]贫民窟的工人阶级摄影进行了考察:
作者首先介绍了利兹历史上不合理开发的问题——政府因为贪图利益而建造棚户区,使得利兹的卫生状况一落千丈,而居住在库瑞山地区的工人阶级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死亡率触目惊心。市政府为此饱受批评,以时任卫生官员卡麦隆(Cameron)为代表的官僚们试图用摄影来进行记录与宣传卫生改善工作。而这些摄影的主题统一——当时工人的生存环境。
卡麦隆向市议会提交了一系列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照片以推动原有区域的拆迁工作。这些照片大都是棚户区脏乱差生活的图像,它们把“需要书面报告进行长篇大论描写的东西”变为“不证自明的”,让观者对于库瑞山居民的恶劣生存环境一目了然。且卡麦隆技巧精湛地解释着这些照片,面对这些照片真实性的质疑,他总能找到说辞:背景被遮蔽是由于广角拍摄、拍摄不好是由于院落太小,照片模糊是因为有光线问题等。于是,这些照片就成为了“呈堂公证”,成为了权力斗争的武器。约翰认为,照相机在此处行使了权威,这是一种“地方机器的权威”,它剔除了文字表述的情感与生活,只剩下了监控在场——这些照片意味着棚户区的工人需要被安排上一种井然、健康的生活。
因而,照片的现实主义解读再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市议会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次拆迁。即便它比起卫生工作这个旗号更像是一场街道修缮计划,拆迁的目的更像是使投资人能够廉价购入这些迁走工人的房产。关于这一点,约翰写道“我们看着拆迁后井然有序的街道的照片,然后问道:贫民窟的工人居民都去哪儿了?”工人阶级只是充当了这场拆迁的旗帜,配合照片被迫表演。而卡麦隆重塑城市景观并重新进行人口安排的梦想,变成了手握内城补偿金的投资者的遗产。可见,照片再次成为了治理艺术的工具。
在对摄影表征的探索中,现实主义的魅影终于使得约翰对其动手。他明确提出要在第六章[12]探讨“现实主义的前提条件”,并将其归结为“摄影与现实的关系”“照片构建意义的过程与程序”“照片的社会功用”“照片的生产和消费的体制框架”这些问题域。他选择了两张照片作为论述的起点[13]。
约翰认为,这两张照片典型体现了摄影的权力:摄影以其“自然”“真实”遮蔽了意识形态关系,简言之就是去历史化。他指出“神话结构所获得的具体性,是以物品和事件失去其历史特殊性为代价的”。两张图片从表面上看都是关于温馨家庭的写照,只不过背景各异,照片作为能指直接链接到了人物与家庭本身。而这两幅照片则被官方作为宣传家庭与社会和谐的典范收藏在国会图书馆中。
然而,恰恰是各异的背景暴露了其阶级差异——一条绘有田园风格的毛毯暴露了这一点;此外,摄影角度也暴露了中产阶级与普通民众的差异[14]。这就意味着两个家庭处于两个不同的阶级,而其阶级的形成则是一个历史过程。约翰打开了这一缺口,并向我们指出照片的真实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宣传的那样美好,而这恰恰是其意识形态的缝合点。约翰援引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将照片的“传播性”置于重要位置:重要的不是谁来拍,而是它被用于表征什么。在约翰看来,照片可以用于各类社会场合,它承载着社会价值进行流通;而恰恰是在其流通过程中,国家作为权力的控制者决定着摄影如何传播,承载着怎样的价值观。而资本主义选择了去历史化的现实主义,恰恰是因为其可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背书——用现实主义为照片镀金显然是机械化大工业的绝佳选择。
于是,照片就成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正如阿尔都塞所言,资本主义力图在静止的照片中让个体获得“社会是由单个的个体构成”[15]这一幻觉,而忽略了其背后的历史铺陈。去历史化的现实主义使得照片没有了厚度,让其机械复制不仅成为了技术事实,也成为了社会事实——而这两张照片被归档,则使其权力更为显著。
因而作者指出,照片说了什么恰恰是权力干预的结果——照片就是话语,并且受到其高度发展的社会体制的激发与支撑。进一步来说,权力通过照片规训主体并生产主体,如福柯所言“禁止、拒绝、禁律,远不是权力的基本形式,而是权力的限制,是沮丧的或者极端形式的权力。权力的各种关系毕竟是生产性的。”换言之,生产合适的照片并使得人们接受它才是权力运作的日常表现形式。而禁止、销毁照片便是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意义上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这皆是为了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行。
至此,我们发现了摄影作为表征所承载的重负:正如前文所言,摄影一经发明,就因其视觉上与现实的高度相似性而战胜了一切模仿世界的艺术[16]。而资本主义巧妙的利用了这一点,将摄影话语用去历史化的现实主义进行统御,使其可以更为直观而不容置疑地表征现实,并宣称自身就是现实。而当这一现实落实在国家层面,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档案的一员,且比文字档案更有直观与不可置疑性。而这进一步增强了档案权力:视觉的现实与话语一同袭来(或者说视觉本身就是话语),使得个体在这一系列的质询中生产出主体,而权力在其中弥散——而这一切都在“自然”“真实”的外表下堂而皇之的进行着[17]。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厘清:既然作者讲到照片作为历史档案而存在,但又强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抹去了照片的历史性,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之处?
这恰恰是本书行文深刻的体现。依笔者浅见,这二者非但不冲突,反而构成了互文印证:作为历史档案存在的照片被抹去了其历史性乍看之下很矛盾,而这恰恰是意识形态的诡计。照片在视觉上能够反映现实,生产着关于现实的“真实之镜”,然而这面镜子是静态而片面的,它过滤掉了历史本身的复杂和动态。在档案中出现的照片事实上是历史的替代品[18],它以欺骗性的面貌成为了历史的拟像(simulacrum)(原相早已不可寻),作为一种话语成为了正统的档案,对社会进行着治理与规训。而这一话语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弥散(dispersion)了,照片这种可见可及的权力话语[除非其成为权力难以统御的神圣人(homo sacer)]发挥着不逊于文字的治理功能。简言之,照片以静态的、片面的姿态掩盖了复杂的历史真实,若非进行细究,我们便难以发现这一症候(symptom)。
当然,这并非是否认照片的功能。应当看到,摄影生产着皮尔士(Charles Peirce)意义上的“图像符号”(image symbols),它有助于我们直观而清晰的感受世界,快速到达其直观所指。但正因如此,我们更要警惕摄影构建的洞穴使我们放弃探寻外部世界而置身于其中。就像桑塔格所言“人类无可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老习惯未改,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摄影中陶醉”[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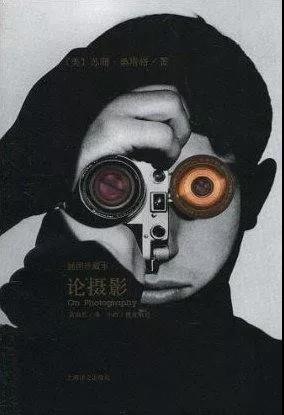
苏珊·桑塔格《论摄影》
[1] [法]亨利·伯格森. 时间与自由意志[M].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3.
[2] 丁华东,余黎菁.论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J].档案管理,2014(06):6-9.
[3]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 1998:166.
[4] 徐拥军.档案记忆观的理论基础[J].档案学研究,2017(06):4-12.
[5] 当然这一说法有绝对之嫌,但不妨碍我们理解档案在社会中的权力。
[6] 何嘉荪,马小敏.德里达档案化思想研究之一——从档案概念说起[J].档案学通讯,2015(4):25.
[7] 事实上,德里达在《档案热病》中同样提出了档案的泛化,他认为“世上所有个人的、社会的、机构的以及技术上的信息交流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档案化过程”,这一论断实际上将档案提升至了全部记忆的高度。
[8] 讲的开放一些,摄影与肉体的关系带着性虐待的痕迹,只不过这里的虐待不是纯粹物理的(SM),而更倾向于精神上的控制(DOMINATION)。
[9] 我们在此应当将福柯对parrêsia(诚言)一词加以简要回顾。诚言指我们应当说的,想说的以及我们认为是真的。罗马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认为诚言是一种政治演讲,是为了统治他人而存在。诚言在福柯眼中同样是一种治理术,但目的是为了实现他人对自我的治理。
[10] 具体请参见《图像证史》。
[11] 利兹是英国第三大城市,是英国重要的金融与法律中心。
[12] 本章实际上是一次演讲。
[13] 由于技术原因,这两张照片可查阅本书P153、P154。
[14] 在此处我们可以比照布迪厄关于摄影的论述。布迪厄认为,摄影是中等品味的艺术,人们通常认为摄影只不过是按快门还原现实而已。但事实上,在不同阶层的价值系统中摄影是不同的(特别是摄影的艺术价值)。对于上层与底层而言,艺术摄影都遭到了排斥,而这恰为意图向上靠拢的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提供了绝妙的区隔。中产阶级通过消费艺术摄影以证明自身拥有一定的“贵族的”“上层的”美学趣味。这一点可观察其拍摄的照片获知。详见布迪厄《摄影:中等品味的艺术》。
[15] 这一论述出自其著名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事实上,这是阿尔都塞在撰写《论再生产》一书中的抽段节选,该书的中文版已于2019年问世。
[16] 这么说并不严谨,事实上,摄影不可能取代艺术,即便是模仿艺术。
[17] 想要考察更为细致的国家权力运作,可参考文献David Sessions. Nicos Poulantzas: Philosopher of Democratic Socialism[J]. Dissent,2019,66(2). 注意普兰查斯与福柯的歧异。
[18] 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实的历史永远不是档案中的历史,无论档案有多么逼真。因为真实的历史仅存在于它自身。
[19] [美]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3.
>>>差异与重复<<<
摄影漫谈
全书第七章是作者编著本书的笔记,他坦承本书具有随笔、即兴的性质。这倒也启发笔者对这一主题展开一点漫谈。当然,这里的漫谈与本书既有重复,也有一定差异。
通常而言,讨论摄影有三本学术著作是绕不开的——分别是本雅明《摄影小史》、桑塔格《论摄影》以及巴特《明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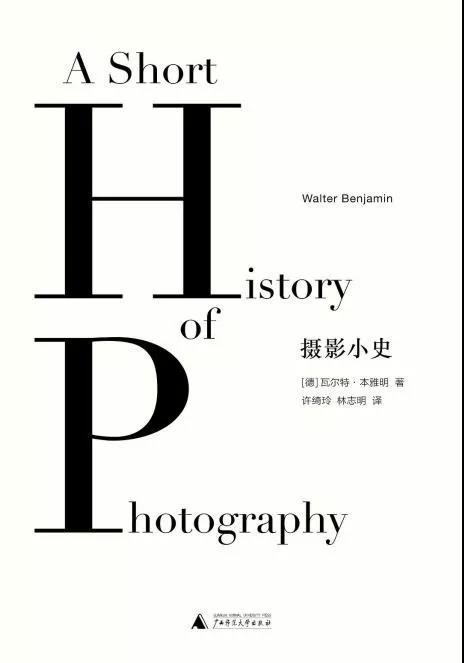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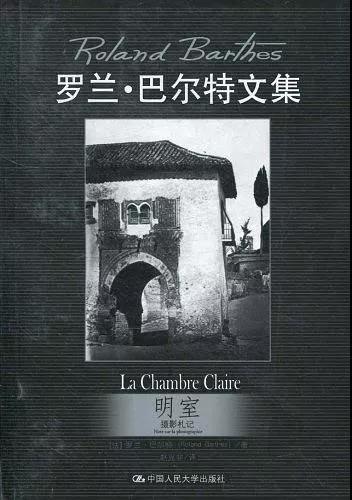
三位对摄影的关注点各异。对于桑塔格而言,摄影是魅惑精灵,使我们重新置身洞穴并自愿带上镣铐观看逼真的舞蹈;而本雅明则关注摄影带来的思想变革,他认为摄影固然消解了“灵光”,但同时其真实性也带来了大众参与政治、消解宏大叙事的可能[1];巴特则尤为关注摄影的“刺点”(Punctum),即“从照片的场景里像箭一样射出来,射中了我”的东西,是照片对情感的穿透与本能的唤醒。三位学者对摄影的看法尽管不相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摄影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而是置身于各类关系中,自愿或不自愿的承载着各种意义——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私人的。
事实上,今日我们考察的摄影早已今非昔比[2]。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被把握为图像”,我们进入了图像及其带来的视觉时代。与本书所成的上世纪70、80年代相比,如今摄影技术愈加发达:照片和视频已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使得影像更为清晰的技术不断被应用于现实生活;同时,图片处理技术也水涨船高且更为亲民,任何人都能够学会并使用相关软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被视觉所包围,目所及处皆能看到各类图像,人物事景无所不包。特别是在媒体充斥的当下,我们不断地收集、凝视、占有而后抛弃——实质就是在消费图片。今日,我们对世界绝大部分的认识都来源于媒介与图像:我们总能看到遥远地区的繁华富庶、奇珍异宝;也能看到异国他乡的战乱频仍、流离失所。摄影不断传达视觉,我们吸收视觉并生产观点与思想。
诚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这些现象早就做过论述,我们也对“拟像”“内爆”(implosion)“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等名词耳熟能详。然而,结合摄影的表征与权力的联结,我们不妨把目光向内回收,来讨论“视觉时代中的摄影与教育”。
这个问题值得写作数十篇论文加以讨论,而相关文献也不算鲜见。笔者在此无意研讨其全貌,仅仅谈一个老问题:校园监控。
这四个字一定会让“全景敞视监狱”再度浮现在脑海中,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分析路径:摄像头相当于监视塔,学生相当于犯人,在全景敞视监狱中害怕惩罚被规训,成为驯顺的肉体。但需要明确的是,全景敞视监狱的伦理底气并不足:边沁(Jeremy Bentham)将其作为模型设计时考虑的是其实用性,他认为中央监视塔是黑暗的还是透明的决定了全景敞视监狱是否会成为暴政的工具[3]。不过,在监控时代,中央监视塔并不需要涂黑,只要隐形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那么,这样的监控是“恶行”[4]吗?基于福柯的分析,我们会认为这是权力规训与宰制的表征。然而,监控与监狱能这样简单地划等号吗?我们在这里沿着约翰·塔格的思路,重新捋一捋这个问题。
监控意味着监视者(教师)观看到的是学生的图像而非肉身——这意味着在评判中影像取代了学生身体真实的在场,教师真正评判的是图像而非学生本人。而在教师进行一遍遍的回看、拖拽、倒放中,图像的权力就越发彰显。
是的,教师真正观看的不是学生而是图像,明确这一点尤为重要。当教师观看监控时,他与学生是空间分离的(通常教师会在监控室或办公室观看监控),这就意味着二者的空间权力也是不同的:对于全景敞视监狱而言,无论处于中央塔还是圆形监狱,囚犯与监视者都共享监狱这一空间。但对于监控而言却并非如此,学生只是作为暗室中用过即弃的底片而存在,真正在场与言说的是图像;同样地,教师评判滤去了活生生的人,而是用现实主义审视去除了“历史与真实”的图像。由此,监控下的学生消失了,他们成了平面中分散的点,教师成为了现实主义的代言人,犹如机器一般对点的运动做出奖惩。规训权力在此翻转了,图像成为了它的执行者。而本该在教育中在场的人在此刻消失了,我们看到的仅是机器的在场及工具理性的运作。
当然,这样的分析有过于绝对之嫌。但当看到如今愈来愈多的学校张贴在公众场合的通告,其惩罚措施仅仅依赖监控探头时,我们便需要意识到:比之监控是否是“善”的,我们首先应当分辨真伪——监控是否是“真”的[5]。换言之,校园监控首先是真伪问题,其次才是善恶问题。通俗地讲,影像只是真实世界的入口,其背后的学生才应当是教师去探寻的对象。但这一浅显的道理,如今经常被技术的直观与方便所遮蔽。特别是当监控作为档案留存之后,它的威力就不止“规训”这样简单。
于是,我们也再次确认了摄影之表征的重负——它是权力的执行者,也是权力的管道,它正在搭建着新的洞穴。而这就要求我们从影像这一舒适的洞穴中走出来,而非仅是陶醉于墙壁。
笔者不禁思索:作为“重返洞穴”的题目并不适切——或许我们从未走出过洞穴,而返回洞穴更是奢谈。但是要能往外走出一步,也算是一份成果吧。
[1] 应当注意的是,与约翰·塔格不同,本雅明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剧烈动荡的时期,彼时苏联方兴未艾。资本主义世界经历巨大变革,摄影对于他而言是革新的钥匙;而塔格的作品则甚少涉及战争时期的摄影。
[2] 本文中甚少使用“影像”。因影像的覆盖面远广于摄影,电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电影有着独特的哲学思考,感兴趣者可阅读德勒兹《运动-影像》《时间-影像》。
[3] 杨思斌.功利主义法学述评[J].安徽大学学报,2005(05):60-66.
[4] 鉴于暴政的政治意味较为浓厚,在此更改表述。
[5] 当然,这里并非是肯定肉眼直接观察即为真实。但监控恰恰启发我们反思所见即真实这一问题。我们以为愈发真实的世界,实质上有可能只是更深的洞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