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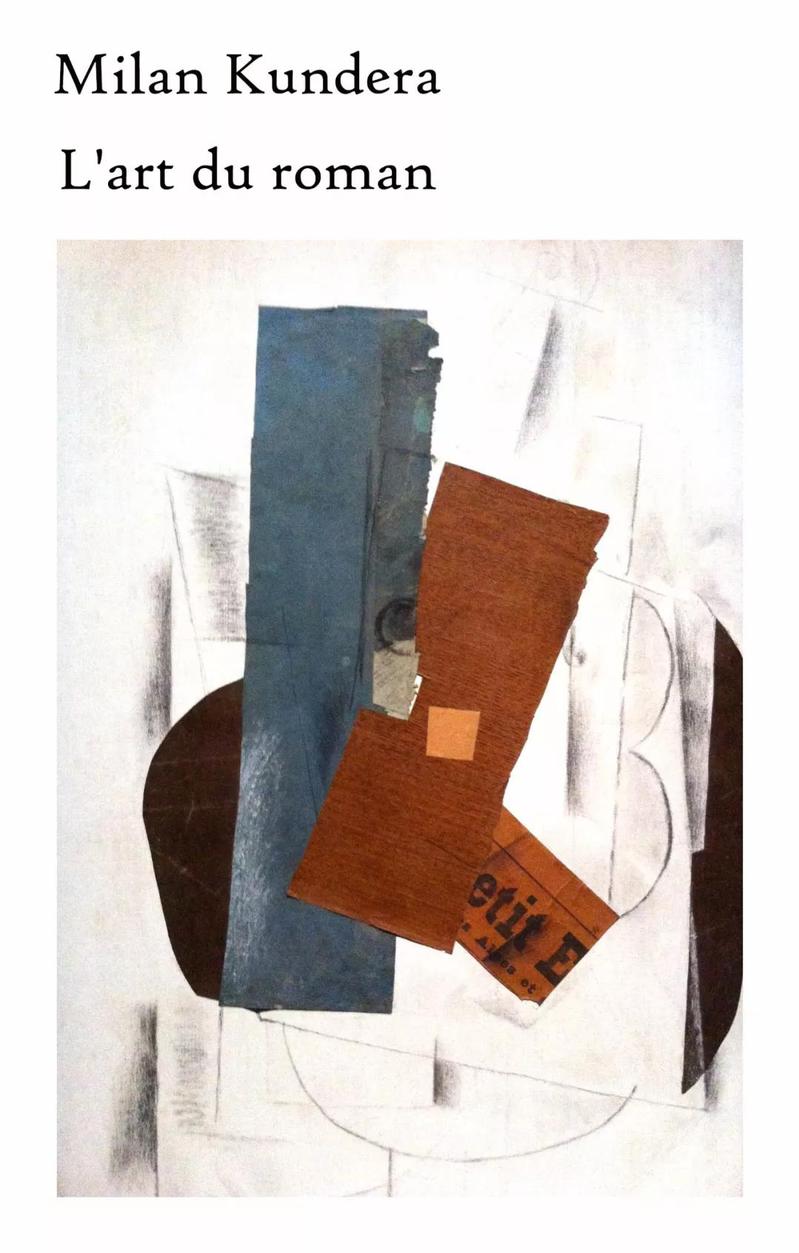
《小说的艺术》原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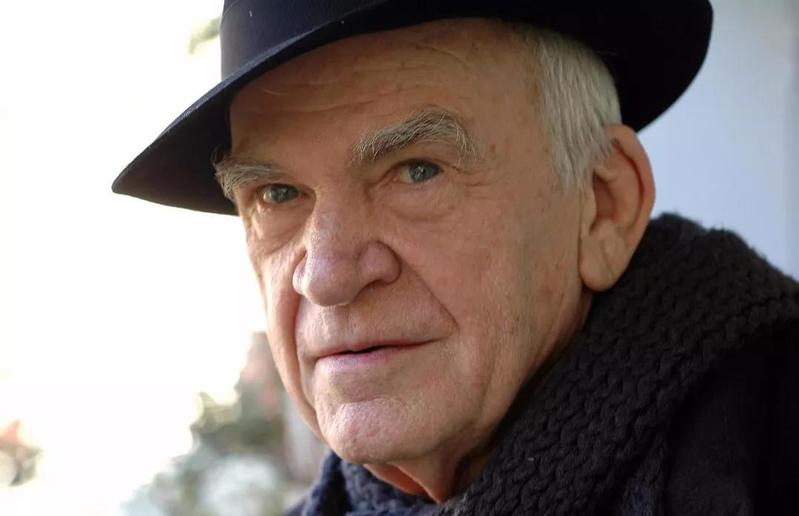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发表于1986年,是米兰•昆德拉1979-1985年间的七篇文章、谈话、札记、词典或演说,它们独立成篇,但经过整体的构思,陈述了昆德拉小说中固有的其关于小说的想法。
在第一部分“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中,昆德拉对小说的艺术进行了概观。昆德拉认为小说乃是对存在的探询,是一种知识,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P6)。胡塞尔曾痛陈欧洲由于抛弃了生活世界而陷入人性的危机,其弟子海德格尔也指出一种“对存在的遗忘”(P4)。相对于哲学家彻底的失望,昆德拉认为过去的现代欧洲四个世纪在理性主义高歌猛进的同时,也有另一条道路在铺展开来,它从塞万提斯开始,直到今天。这条道路是小说走过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小说家们承继塞万提斯留下的遗产,前赴后继地对人的存在进行了自己的探询。由于小说的未来不甚乐观,对这四个世纪的探询之路,昆德拉深表眷恋。堂吉诃德走出家门的时刻,正是上帝离开他的宝座的时候,最高的非理性价值跌落了,世界变得暧昧不清,伽利略和笛卡尔带来了科学真理和人的理性,让复杂变得简单,让暧昧变得黑白分明,但正是堂吉诃德和塞万提斯保卫了世界的暧昧性,在科学的确定性智慧之外开拓了小说的“不确定性的智慧”(P8)的领地,这一领地为后来的小说家提供了家园。从堂吉诃德到土地测量员K(出自卡夫卡作品《城堡》),小说的种种人物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是欧洲人走过的现代历程。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发现是堂吉诃德自己从村庄走入城市,从田野走入警察局、法庭、军队和国家,他从冒险到怀念冒险,从远方的旅行到心灵的迷途,最终跌入了一个陷阱当中,换上土地测量员的行头回到村庄变成了K。K的时代被昆德拉称为“终极悖论的时代”。K被一份错误的档案指派到城堡担任土地测量员,由于这是一次错误的任命,城堡拒绝给他这个职位,K千方百计精疲力竭地想要进入城堡就任,却至死也未能成功。理性摧毁了上帝,却让纯粹的非理性占据了世界的舞台,这是终极悖论时代的悖论之一。冒险、未来、罪、喜剧性、孤独、私人世界与公共世界,这些主题在终极悖论时代得到了不同的探索。昆德拉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
第二部分是一份关于昆德拉小说美学的谈话稿。昆德拉首先从他的小说不是心理小说谈起。根据小说如何探究人的自我,可以将小说划分为不同倾向甚至不同历史分期。小说从最开始(如薄伽丘)是从行动来表达人的自我的,到了狄德罗则发现了行动的悖论性,即行动与自我认知之间并不符合,人甚至要在行动中认识自己,而不是根据自己来做出行动。小说对自我的认知于是从行动转向了心理。歌德、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等都是小说探究人的内心生活的高峰。然而这一条道路行至乔伊斯也显出了悖论性,“观察自我的显微镜的倍数越大,自我以及它的惟一性就离我们越远:在乔伊斯的显微镜下,灵魂被分解成原子,我们人人相同”(P32)。悖论性的告终并不意味着任何失败,对自我的探究终归要走向悖论,但每一次显出其局限都是巨大的发现和认知的成果。卡夫卡在人的行动和心理之外发现了新的力量:权力(福柯意义上的)的力量。昆德拉本人则使用另一套把握自我的办法:直接探询自我存在问题的本质,“把握自我的存在密码”(P38)。这使得其小说中常常出现一些“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从人物的行动和处境中生成,昆德拉通过对关键词的直接沉思,使人物自我的存在本质得以显现。而借由这种对存在本质的探询的直接性,也使得其探询具有了额外的普遍性,人物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形式,其实质是一种人类存在可能性,或者一种用以理解存在之可能性的“实验性的自我”(P40)。人物在这里不再追求真实(像写实主义那样),他们没有刻意构造的童年、家庭背景或外貌,没有特定的说话方式或行为方式,但并不因此而失去生动性,并不因此失去读者的代入感,只是这种生动和引人入胜借由另一种方式,一种思想性的方式得到了实现。这种对存在的探询也带来了另一个结果,即小说的社会历史性。常常有人对昆德拉的作品做出社会学、历史学或意识形态的阐释(这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这是由于昆德拉将人的存在理解为一种立体的存在,他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说法“世界中的存在”来表达这一看法:人并非是一个孑然独立的人,而是像蜗牛一样与世界连为一体的人,世界乃是自我的一部分。因而在他探询人的存在问题的同时必然地涉及了社会和历史的存在。由于其出发点的特殊性,昆德拉处理历史时带有几个原则。其一,历史背景以最大的简约来处理,就像他的人物形象那样;其二,只采用能为人物形象营造出一个能显示他们的存在处境的背景,并不书写历史本身;其三,写人的历史,而不是像(传统)历史记录那样关注社会的历史,因此他常常涉及一些被历史记录遗忘的东西,例如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几次灭狗行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历史本身也必须作为存在处境来理解。例如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杜布切克(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被俄罗斯军队逮捕,绑架、关入监狱、威胁,不得已与勃列日涅夫交涉后回到布拉格,他在广播上讲话,但说不出话来,“在话与话之间作出长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停顿”(P48)。这一历史片段在小说中与人物特蕾莎的处境一同加以探究,它是“一个集体的、历史的处境”,这里的关键词是“软弱”。也正是由于其对历史的态度是一种探究存在的方式,昆德拉否认小说与历史之间有任何符合关系,小说既不是对已发生的书写,也不是对未发生的预言,它是对存在之可能性的探究,其对历史、社会与政治都处于一种“非介入”状态(参见第五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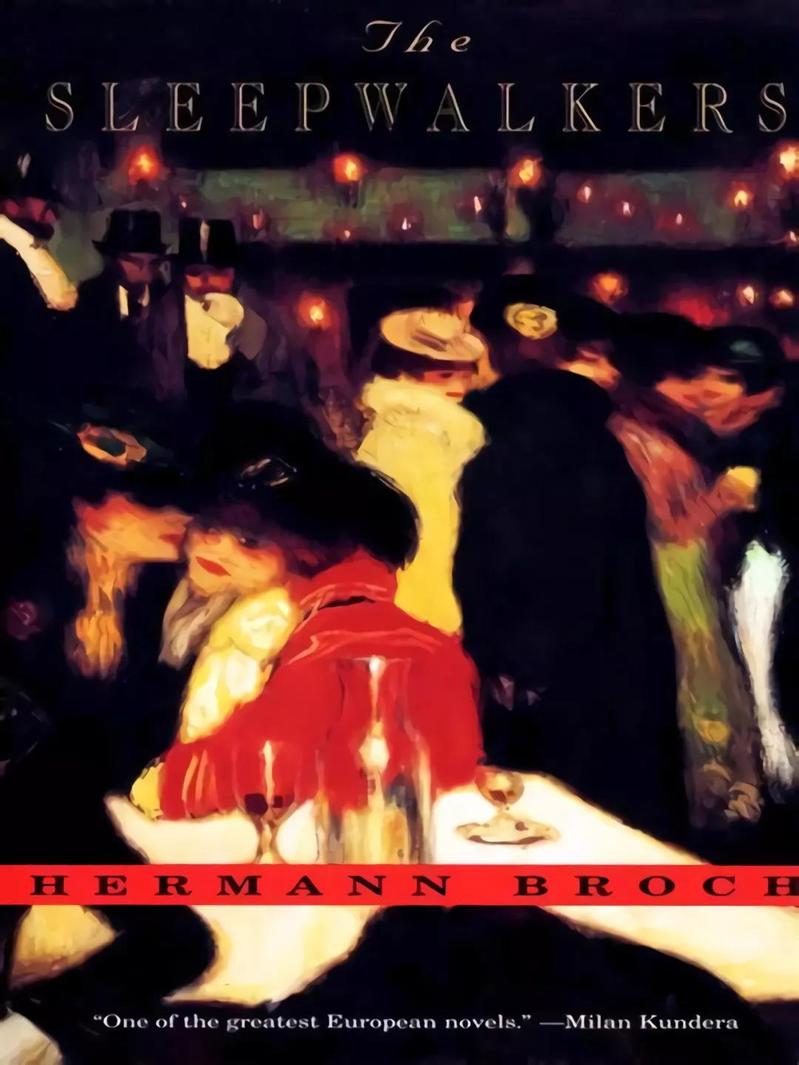
《梦游者》原版封面
第三部分是昆德拉针对布洛赫的作品《梦游者》而作的札记。《梦游者》由三部小说组成,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尽管有重叠的人物),而由一个共同主题形成一致性和延续性:一个人如何面对价值贬值进程。要对人的存在可能性进行探究,首先需要一个对世界的本体论假设。这个假设在卡夫卡和哈谢克那里是一个官僚主义化的世界,两位作者分别撰写了可能性:约瑟夫•K面对莫名其妙的判决千方百计为自己加上罪行(出自卡夫卡作品《审判》);帅克在莫名其妙的战争中快乐地模仿周围的世界,将一切转化为玩笑(出自哈谢克作品《好兵帅克》)。昆德拉说,“我们的生活空间一方面受到了K的可能性的限制,另一方面则受到了帅克的可能性的限制……我们生活空间的一极是跟权力的同化,甚至受害者跟自己的刽子手产生默契,另一极则是对权力的拒不接受,其方式就是不把任何事当回事”(P62)。对布洛赫来说,世界则是源于中世纪的价值之贬值的过程,这一贬值过程是现代的本质。在这一假设下,人的可能性有三种:依赖继承的价值,将世俗的制服作为新的绝对权力;一切都可看作价值,但一切都不清不楚,似乎陷入迷狂或永远四处冲撞;无道德的自由,成为世界的刽子手。三种可能性分别在《梦游者》的三部曲中借由三个人物得到探究。三种可能性加上K和帅克,构成了五个方向标,画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地图。如此,三个人物(也可说五个人物)也不再是他们自己,而更是“跨越于时间之上的桥梁”(P70),勾连着数世纪天穹下的历史和人类。
第四部分是一篇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昆德拉小说的结构艺术奠基在他对小说艺术和美学的理解上,并凸显着他受过的音乐教育的影响,呈现为两种形式原型。第一种最为主要:将异质的元素统一在建立于数字七之上的建筑中的复调结构。音乐中的复调指两个或多个声部同时展开,昆德拉用来指以相同主题统一起来的小说的多线结构,这在布洛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出现。异质元素可以是小说、短篇小说、报道、诗歌或随笔,而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更多出现的是叙事和随笔的结合。随笔对昆德拉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提出一种“小说特有的随笔艺术”(P85),这与其“探究存在”的艺术观念密不可分。随笔即一种直接呈现的思考,纳入小说中的这种思考不表达人物的观念,也不表达作者确证的想法,而具有假设性、游戏性和探询性,它们服务于对人物处境的探究,就像上文提到的那样。数字七则是一个非理性的数字,它是昆德拉在写作中无意识地呈现出来的规律性,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小说各部分之间的长度、节奏等清晰的环节或结构特点。第二种形式原型只出现在《告别圆舞曲》当中,这是昆德拉唯一一部以五部分组成的作品,它是一种滑稽剧式的结构,代表了小说的娱乐性或游戏性传统。
第五部分讨论了昆德拉的另一位导师(我们很容易看出其第一位导师正是布洛赫),即卡夫卡。什么是卡夫卡式的?我们从K和约瑟夫•K的故事去思考。第一,权力的无边无际的迷宫的特点,谁召唤K来到城堡,或谁为约瑟夫下了判决?他们面对的是像迷宫一样的权力世界。第二,人变为一种错误的存在,K被错误的档案派来城堡做土地测量员,却发现没有这份职位,他不仅是档案的一个影子,而且是错误的档案的一个影子,一个无权作为影子存在的影子。第三,不是过错带来惩罚,而是惩罚召唤过错。约瑟夫•K将要被惩罚,他只能乞讨一种罪过以使惩罚具备意义。第四,将悲剧喜剧化,使悲剧失去救赎的可能。K或者约瑟夫•K的故事都是可笑的,但卡夫卡将我们带入玩笑的最深处,体验彻底的悲剧。像上文提到的,小说并非是历史或现实的改编,也不是未来的预言,而是对存在的诗性探询。卡夫卡的作品也是一样,我们能在现代历史的一些时期中感受到“生活就像是卡夫卡的小说”,但不意味着这些作品特定地书写了任何时期或社会,而那些看似与此无关的社会或时期也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这些存在可能性的隐隐约约的影子。作为诗的小说是悖论式的,其“巨大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以及‘预言’意义都存在于它们的‘非介入’状态”,存在于“它们相对于所有政治规划、意识形态观念、未来主义预见而言所保持的完全自主性中”(P149)。
本书最后两个部分,其一是一部有关昆德拉本人的六十七个关键词的词典(用以对抗其作品的各种译本对其本人和作品的歪曲),其二是昆德拉在耶路撒冷的一篇演说。两个部分都构成对上文的映衬和注解,也具备一些新的内容,尤其是关键词一部分,但赘述的意义不大,本文就此略过。
回顾本书,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津津乐道于胡塞尔及其后来者是如何寻找遗失的生活世界的同时,昆德拉提醒我们可将目光转向欧洲四个世纪以来的小说家们,他们为捍卫生活世界做出了令人敬仰的努力;第二,除了生活世界以外,“权力”、“科层制”等社会学概念也在小说家的作品中得到了讨论,尽管这种讨论是以非理论的话语进行的,但依然值得我们去注意和吸收,不论是其探究的内容还是方法;第三,尽管年鉴学派后的历史研究已经有了比较广阔的视野,但昆德拉在小说中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灭狗行动的关注依然提醒我们,带着“人”的视角去注意一些不为人知故事;第四,小说的“不确定性的智慧”颇具后现代色彩(或者后现代带有小说艺术的色彩),如何在后现代知识观假设下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许在小说的艺术中有所启示;第五,昆德拉自身小说实践坚持的简约性、复调结构、随笔艺术等手法,以及将人作为“世界中的存在”来考察,对如何实践叙事研究方法有突出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