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维尔纳·桑巴特.2005.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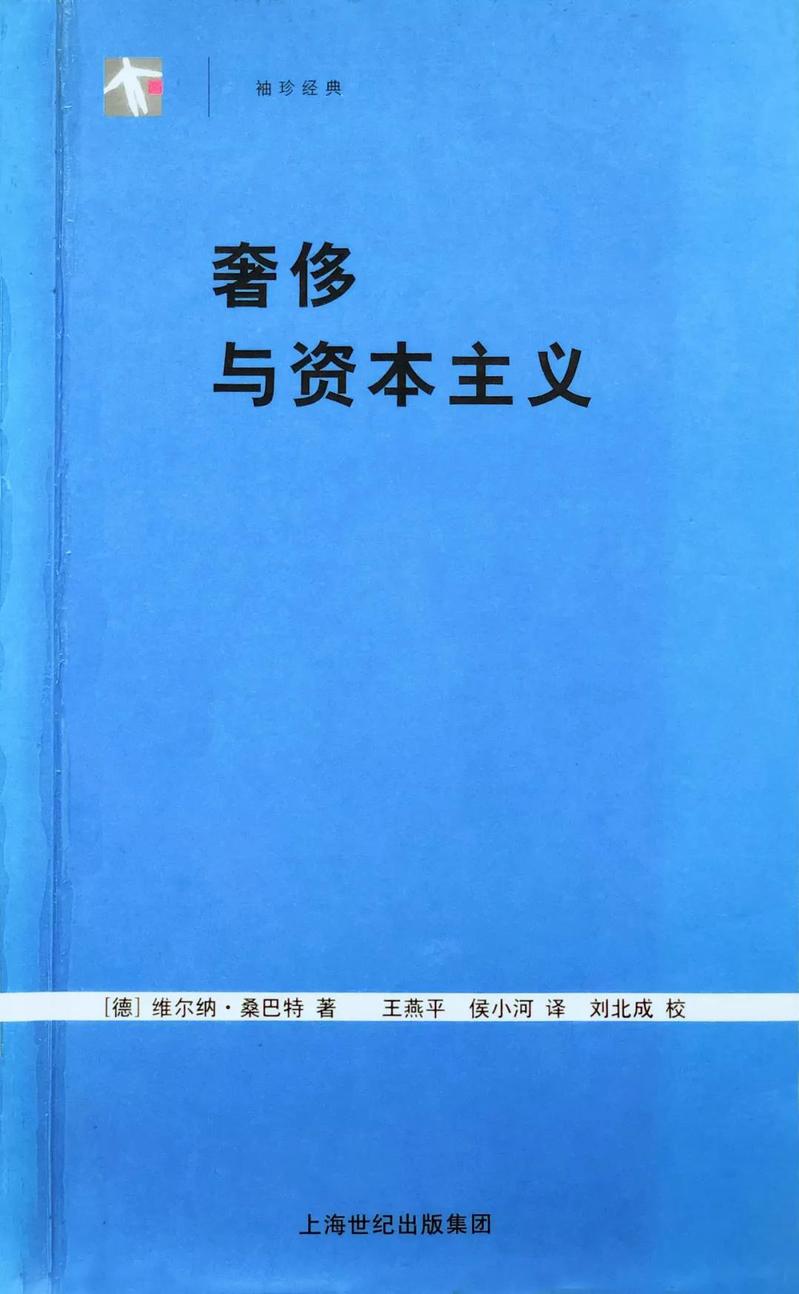
“巴黎不是属于女人的吗?而女人不是属于我们的吗?”[1]
——左拉小说《妇女乐园》中,慕雷对哈特曼男爵所言
比之于今日要推介的《奢侈与资本主义》,恐怕使人联想到的是我们的一位“老熟人”——马克斯·韦伯——的著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名文本的形式相似使我们仿佛可以推断:若要对于资本主义动力机制做一番溯源,桑巴特与韦伯则不可避免被连在一起。自1904年始,韦伯与桑巴特就相识并共事于《社会学与社会政治学文献》(以下简称《文献》)的编辑工作,而韦伯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便脱胎于最初发表于《文献》的若干篇掷地有声的撰文之中。
桑巴特作为仅比韦伯年长一岁的同龄人,共同成长和浸淫于“德国思想”时期,而这是德国社会科学的学科版图正处于各个联经点的汇流与形成阶段。创建于1873年的德意志经济史学派[2]聚合之初衷在于对英国政治学经典与惯例长久以来的抵制与反叛,特别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充分代表和维护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利益,这在当时依旧处于农业经济的德国思想家眼中,一方面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更为致命的,是一种长久的抽象而虚幻的普遍性的线性增长史观,其代价是对文化、社会、历史等等因素考察的付之阙如。
在桑巴特之前,德意志经济史学派中亦不乏对于“奢侈问题”的大量研究,这其中包括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然而将奢侈武断地划分入道德范畴的批判性基调是不能令桑巴特满意的,它割断了奢侈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积极联系,而这正是桑巴特所认为的奢侈作为一种需求系统所开启的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市场。在他的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中,他考察了贸易业(包括批发与零售业,他还特别强调了殖民地贸易),农业,工业领域(他界定了纯粹奢侈品工业与混合工业)对奢侈需求的回应,并且证明正是奢侈将这些行业纷纷导向精细化的改进道路,并同时催生了新的追求生产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精神,传统奢侈品制造业也在此过程中转变为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企业,最终孕生了资本主义独特的生产机制与经济秩序。
他强调资本主义独特的进化过程是内部相互依存的文化综合体的表现形式,其方向则是由量化的理性精神为其指明的,这种理性注入文化统一体,为其确立了特殊的个性与目的。[3]有可能以既统一又特定的方式阐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端原因中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原因的多元与复杂并不导致不确定性,而是相反,它指向“由多种原因决定”,从而致力于重构表现在社会文化特别是物质文化与性价值观变迁中的复杂关系网。
作为韦伯的同代人,桑巴特与韦伯在资本主义起源的歧见在德国政治经济学派中是相当值得瞩目的,歧见的持存或许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桑巴特对于资本主义动力的溯源更有所助益。[4]雷蒙·阿隆曾对造成这一主要分歧的原因作了较为本质的概括,即在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概念界定之差异[5],桑巴特倾向于将“资本主义”定义为受无限获取财富的欲望驱动的经济体系,欲望向外衍射的且没有界限,以交换和金钱、以财富的集中与循环,以理性计算为特征。而在韦伯那里,新教伦理作为一种内化于个人的克制与审慎的宗教观念,将诸种非理性化的欲望加以理性化的节制,在对上帝感召(calling)的持续追寻中恪尽致富的伦理义务,使得资本盈利的积累最大化,从而孕生资本主义精神。导致桑巴特对于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与形成要素是通过将资本主义作为整体进行把握而描述出来,而不是采用韦伯的方式,在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得出的[6]。而桑巴特的论述显然因缺乏这一比较分析,因而无法解释为何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巨额财富的累积以及大规模的奢侈行为——这被桑巴特视为资本主义孕生的重要条件——却最终难以肇端资本主义精神。这显然是一种极不平衡的分析,出于上述理由,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并不蕴藏在奢侈——作为人类社会自然而然的现象——在世界各处皆发挥着影响,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要素而言显得无足轻重。[7]也成为使桑巴特对资本主义动力起源追溯被广为诟病的一点。
雷蒙·阿隆对关于资本主义动力的因果研究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精炼:简言之,因果研究可分为两种路径,历史学上的因果关系与社会学上的因果关系,前者决定导致某一实践产生的独特的条件与环境,后者则意味着要在两种社会现象中确立一种固定的关系,此种关系的形式未必是现象A必然导致现象B的产生,也可以使现象A程度不一地促动几乎和助推了现象B的产生。[8]而两者密切联系,其表现形式皆为可能性。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理解桑巴特虽然对奢侈作了历史实证的追溯,但却倾向于一种社会学的因果研究。但是,他的独特视角也使后继学者将焦点从经济与技术性的溯源转移到一些更为隐蔽,更容易被先前所忽视的领域,如大众文化、价值观、性别关系等方面。
资本主义早期巨额财富的积累过程与都市化的形成占据了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的前两章的论述,在这期间,巨额财富积累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业已具备,14-16世纪,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大量联姻形成了新贵族阶层,“几乎所有贵族之妻的嫁妆都直接来自于银行家的保险箱。”[9],一旦财富可以自由表达,皆可见奢侈之踪迹,新兴的贵族的财富表达欲被桑巴特援引凡勃仑的观点阐释为在攀比与区分的心态下“出人头地”的欲望,在这和追踪欲望驱使下,新兴贵族很快与封建贵族融于均质的整体[10],而城市的财富吸引了大批逸乐的追寻者,消费型城市逐步在这种扩容的需求中形成,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皆为消费型城市[11]。

凡尔赛宫内部洛可可风格的室内装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早期的消费型城市中,除了享乐为主的王公贵族,有相当一部分则是以为贵族需求提供服务而生的人口,并不从事生产型作业,[12]这与桑巴特稍后对于生产性的奢侈与非生产性的奢侈的划分形成一种初期的对应关系。[13]桑巴特认为,个人的奢侈是非生产性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奢侈的客观化趋向,集体的奢侈的则倾向于一种生产性。
在奢侈个人化与非生产性所致的客观化过程中,性别关系在社会生活迁变中的重要性浮现出来。桑巴特考察了中世纪以来传统性价值观、性道德观与情爱观的嬗变,原本屈从于宗教秩序的性别观念被赋予世俗化色调,大量欧洲游吟诗人对于自由情爱的颂扬的诗作,以及15世纪艺术领域中裸体女性形象的作品(波提切利《春》),特别是首次出现了对于夫妻关系的描绘和再现[14](扬·凡·爱克《阿尔诺芬尼夫妇像》),皆为桑巴特对于此时期自然肉欲的回归以及情爱空前成为生活之精髓的观点作出佐证。
然而,与自由情爱永远无法协调的是来自婚姻——情爱的人为制度化与神圣化——的规制。然而,自12世纪中叶至16世纪,“人的发现”为性观念的逐步松动注入思想力量,性越来越少地从属于宗教的原则与目标,蒙田在这其中推动了自由情爱与婚姻的观念二分化,大城市娱乐业的繁荣以及享乐主义的浮荡世风亦为情爱超逸出合法婚姻提供滋生土壤,[15]继而在某种程度上为18世纪“非法情爱”确立自身的价值与地位以及与合法婚姻的并存提供了社会接受度,将曾经在中世纪指向宗教的婚姻生活也置身其外:“女人变得有女人魅力、漂亮和可爱的才能,丝毫不会因为像婚姻这样任何的人为的社会制度而增减其渗透力。”[16],享乐主义美学赋予“非法情爱”以超逸于法律之外的正当性,在这个时代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与唯一的合理性。正如桑巴特所概括的“这是一个灵魂和理智达到前所未有的一致的世纪,是一个爱女人则意味着爱美,爱美则意味着热爱生活的世纪”。[17]
因此,在合法配偶之外蓄养一个文雅的情妇已成为贵族王公们最为热衷的时髦,他们不再因有婚外情与私生子而难堪,反而成为其夸耀自己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筹码。非法情爱作为一种上层男性以资炫耀的象征资本,经由社交生活渗入宫廷。桑巴特觉察,一个新的女性阶层出现于受尊敬的女性(贵族的正室)与浮荡的女性(高级妓女)之间,“情妇”[18]则成为这一类新出现的女性阶层最具代表性的指称。桑巴特转而关注这些在“非法情爱”中获得权势的女性——情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欧洲的生活方式。而在历史上成为这些“快乐与趣味仲裁者”的女性,我们可以列一张相当漫长的清单,这其中包括路易十五的权倾一时的情妇蓬巴杜夫人与杜巴丽夫人,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等等。

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
当我们在艺术史中观看一种被称之为洛可可[19]风格的画作与家具风格,这不得不提到蓬巴杜侯爵夫人,作为18世纪法国宫廷最为显赫的宫廷情妇,被路易十五称赞为“完美无瑕的奇迹”并授予爵位。此后,蓬帕杜夫人坐在路易十五的宝座旁与龙榻上,“垂帘听政”长达19载,这期间她对妆饰别出心裁的孜孜追求,同时监制宫廷戏剧、参与城堡的设计与装饰、投资新兴的法国工业,她奢侈精致的审美趣味与艺术造诣对后世艺术风格影响甚广,推动了具有强烈女性特征的洛可可风格,或许在这一层面,蓬巴杜夫人对于一种时代艺术风格的逐步确立而言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推手。
而合法配偶也并不比情妇挥霍的少,甚至极尽疯狂。一部以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为原型的影片《绝代艳后》(2007)对法国宫廷纵情享乐于声色影像中的复原,或许可以作为对桑巴特提及的合法配偶的奢靡所缺失的穿越体验的弥补。在影片中,能使宫廷上下为之震动的不是天下君民大事,而是玛丽王后为哪件礼服增添了何种新配饰。这位王后的奢侈最终以巨额赤字将法国卷入革命洪流。

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
因此,宫廷中被赋予权力的女性,不论是合法与非法情爱中的女性,带着闪光的魅力守候于王权之侧,而她们所“支配”的人在王权宝座上赐予她们代理行驶权力的权力,她们成为社会风尚中的女王,成为快乐与趣味的制造者与仲裁者;她们给琐碎的小事罩上无比重要的形式化的外衣,给所有装饰风格加入逃逸出经济必然性的准则。[20]以求她们卖弄风情的欲望和女人的野心得到满足。
奢侈很快逸出宫墙之外,在不断发展的都市中,众多女性开始仿照宫廷情妇的逸乐和奢靡来安排生活,在对家庭以及居住空间内部的装饰趣味在奢侈下的影响。此时,桑巴特切入了奢侈的本质与奢侈形式的分化,特别是他认为“质”的奢侈本质上来源于被激发的官能,“几乎所有的个人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生发的”,但归根到底,情爱与性快乐正是要求精制和增加感官刺激的手段的根源,因为感官逸乐和性快乐在本质上是具有同源性。在他所援引的类似于弗洛伊德“性的力比多”的阐释中:推动任何类型奢侈发展的根本原因,几乎都可在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起作用的性冲动中找到。[21]
感官逸乐引诱着那些一心意欲享乐的贵族,进而衍生出奢侈的个人化倾向,这是一种新的性价值观与消费道德观在社会生活变迁中发生的同步嬗变。桑巴特所觉察到的正是许多将视线聚焦于经济与技术的史学家所长久忽略的。
任何使眼、耳、鼻、舌、身愉悦的东西都趋向于在日常用品中找到更加完美、精致与敏感的表现形式,感官逸乐与典雅精致成为生活风格必不可少的元素,同时,气息作为奢侈感官逸乐需求促动了香水制造业的发展,大量色情主义与恋物主义生活风格的滋生亦与此有关。[22]于是奢侈的官能化与精制开始紧密相连。
生活模式与奢侈需求体系的深刻变化随之一方面导致了精制的必然性发展,另一方面导致奢侈品行业生产周期的大幅缩短,“女人们没有耐心,而跌入爱河的男人也是如此”[23],因而那些抓住权力浸润于享乐的女性,将个人的生命长短便成为其享有的尘世逸乐的尺度,她们急于享用奢侈,工匠们如同上足了弦发狂的为雇主劳作,于是便有以前时代难以想象的惊人速度建造完毕的奢侈宫殿与奢侈精制品。至此,奢侈的集体模式代替了奢侈的个人模式。
继而,桑巴特以贸易业(包括批发与零售业,他还特别强调了殖民地贸易),农业,工业领域(他界定了纯粹奢侈品工业与混合工业)对奢侈需求的回应,并且证明正是奢侈将这些行业纷纷导向精细化的改进道路,并同时催生了新的追求生产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精神,传统奢侈品制造业也在此过程中转变为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企业,最终孕生了资本主义独特的生产机制与经济秩序。
性价值观的迁变可以说是桑巴特对于资本主义动力学阐释的最为具有原创性的论点所在,他将我们的视线引入社会体系中原被遮蔽的性别与宗教的领域,尤其是他觉察到了女性对于奢侈消费的独特的、且在他看来具有被称之为“统治性”的促动作用,诸如其所描述的女性风格取得空前统治地位的宫廷中,柔靡、具有强烈女性性特征的洛可可风格最终取代以男性特征为表征的巴洛克风格,桑巴特把这一类现象归功于“女性统治的大获全胜”。
无可否认,女性确实在奢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促动因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4]。然而,奢侈真的是全然属于女性的胜利吗?女性风格的统治性与促动性作用是否可以全然视为直接因果关系的范畴呢?
事实上,奢侈的趣味可能并不为上层女性所独享,统治阶级的男性同样追求仪表与居所的奢靡,对于感官逸乐的追逐使得统治阶层的性别配置的审美差异上达到某种程度的共享。布尔迪厄的阶层区隔理论认为:随着一个人的社会等级的升高,由社会构成的性别之间的总体差异其实在减弱[25],性别之间的分工与性别伦理的表象呈现出一种更为暧昧的样貌。在这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性别配置与性别审美并不像民众阶级一样,在一切涉及性别分工高的方面都恪守一种过分严格的道德,将审美或形式追求专门制定预留给女性。
换言之,统治阶层中的男性几乎和女性同等程度得要求精致的外表与装饰,参与雌性竞争中来,并显示出有可能被诟病为“娘炮”气质与致趣,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历史上那些在民众看来过分注重自己的容貌与衣饰的统治者,诸如热衷于假发与香粉的路易十六,钟情于天鹅绒、珍珠与蕾丝花边的白金汉公爵,以及那些意欲在时尚领域中谋得高地位的低位者不得不佯装自己是同性恋方能显得自己比直男更有品位的事实;而与此同时,宫廷中的女性,倾向于取得更多原本最为典型的男性特权,诸如侧身于王权宝座的另一端“垂帘听政”,或阅读表达鲜明政党观点的报刊,甚至参与竞选等等典型的雄性竞争活动中来,这可以解释蓬巴杜夫人在宫廷中对于社交风尚以及艺术风格所施加的影响与辖制。同时,女性长久以来的人身依附性与暗含于经济因素中的性别秩序,是桑巴特在性价值观的论述中所阙如的。
可以说,被允许奢侈的权利看似给予了女性统治空间的独特与稀缺性,然而它源自于一种“甘愿的被拒绝”:即在物质上享有特权又被排斥出经济权力现实的上层女性,以一种同谋般的拒绝来抵制其无法真正据为己有的宫廷世界,这种“被拒绝”于是在审美或唯美主义倾向中找到其特别的表达出口,如若不在审美上寻求一种避难所或回馈,那就在宫廷生活的外观与装饰方面找到她们的成就。因此,女性对于装饰与妆扮等等琐碎而形式化领域的投入一方面出于性别秩序,另一方面,性别秩序在形成这种配置作用如同发挥了颠倒的“皮格马利翁效应(Effect Pygmalion)”[26]或“习得的软弱性(learnedhelplessness)”[27]:她们不需要具有除了外表与家事以外的知识,反正也不适合她们,因而亦没有努力的必要。
这足以解释茨威格笔下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她被描述为一位平庸的女性,其宫廷教师曾评价“她比人们长期以来所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可惜直到13岁还没有养成专心致志的习惯。她有点懒惰,又很轻率……我没有办法使她深入探讨一个问题”[28],“她说话没有下文,思考问题没有结果,阅读半途而废,做任何事都无法专注,都无法从中汲取现实生活经验中的意义和精华……对任何严肃的、需要忍耐性和注意力的事务都漠不关心。”[29]这促使她远离与真实世界的所有特征的接触,而轻盈的将自己抛掷入形式化的感官享乐中去。
因此,宫廷的奢侈弥散入几乎统治阶层以外的所有普通女性:“她们讲究形式与美学上的奢侈,作为男性统治的特定受害者但同时也是将男性统治作用传递给被统治阶级的指定工具[30],她们好像被与统治模式同化的渴望攫住了一般——正如她们具有的美学和语言的过度校正倾向所表明的,她们特别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把因为与众不同而奢侈的统治者的属性据为己有,尤其借助特定状况下的象征权力,促进这些属性的强制性传播。”
桑巴特并未否认,在成为宫廷中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女性的同时被赋予权力,这是与君主统治相伴而生的附属物——性别秩序——它自然而然的要求处于象征交换中的女性对于身体外表的一种极端而持续的关注和保持诱惑的禀赋,诱惑的符号以最传统的方式被分配给女性的角色,而奢侈满足与助长了这种禀赋。
鉴于性的原始性与先于文化性,致使人类社会中对于性的防范是长久而持续的,原因在于性自由可能会销毁一切后天的,用社会力量构筑的身份,性的泛滥“足以扰乱社会结构,破坏社会身份,解散社会团体”[31],然而正是性,或者性优势,如常见的美貌,性感等,常被试图逾越阶层结构的女性以资利用,而处于合法地位的女性则因察觉到这种妄图而不得不发起防卫与竞争。这可以说明为何在欧洲宫廷与贵族中的女性——以情妇为典型,同时也包括为确保自己地位而暗中不得不与情妇展开雌性竞争的合法王权的王后——的服饰具有鲜明的夸示与放纵性享乐与性展示的倾向,如紧身褡,低胸礼服裙,蕾丝服饰等等。
因而,桑巴特也同时看到,在野心勃勃试图僭越阶层进入宫廷获得宠爱的轻佻女人之外,合法配偶不得不调整自己庄严的服饰,在时尚与趣味方面亦步亦趋地紧随情妇们与高级妓女的步伐,并于她们展开雌性竞争,以确保自己在社交生活中的地位。桑巴特承认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文化准则”[32],因为在宫廷中,“每一个女士,不管她的社会地位多高,都必须遵守这些规则。”[33]规则与对于规则的焦虑以阶层时尚的逆向易变为表象,而其根源显然来自性别秩序的辖制,通过对于东方世界——中国近代社会中——上层官员的正室,常常派仆从去青楼观察名妓的时髦妆饰以便暗中效学,上层端矜女性不得不对轻佻女性亦步亦趋。这表明,性别秩序在西方以外的社会生活上演着同样的戏码。
如若以凡勃伦“越位消费”[34](vicarious consumption) 视角对情妇们的奢靡挥霍进行审视,情妇们首先是通过一种足以“越位”的身体表象来结缔“非法情爱”,继而实现社会阶层的僭越并进行“越位消费”,特别是那些出身卑微,却具有美貌又工于社交而跻身宫廷,沐浴在因本不属于自己而不合法的情爱光辉中——去看看杜巴利夫人的轶事就可知,一位下层妓女是如何一步步攀升为路易十五的情妇。在僭越等级的过程中,情妇们的身体遵循着身体的等级空间的逻辑,布尔迪厄将美貌视为其身体的社会表象,是在与其他基本属性的分布结构中严格相称的一种价值,[35]同时具有生物继承性和社会继承性,然而生物继承性的逻辑相对于社会继承性逻辑更有自主性与先在性,比如“老天赏饭吃”——一些美貌是天生的。因此,就有另一种“越位”在不断地在强调生物性继承的偶得先在性与稀缺性中展开叙事逻辑,体现在美貌作为一种最稀有的天赋禀异,会以极不平衡的形式降临于主体,比如给予其他属性方面最为贫乏的人以美貌,这一身体表象随之带来其他属性在社会分布结构的不对等倾斜。换言之,人们常言“致命的美貌”,本质上在于这种身体属性与“性”具有同源性,其配置的稀缺性足以僭越身体的等级空间并威胁社会等级秩序结构。
然而,这种依附性致使她们奢侈的权力随时可以像午夜过后魔法褪去的灰姑娘变回平民女孩一般,随着王权的湮灭而被收回。在路易十五罹患天花病逝后,杜巴利夫人被放逐至修道院,曾被馈赠价值不菲的项链亦被宫廷收回拍卖。大量情妇轶事与史实这可以表明,即便是位处统治阶层内部的女性依旧不可避免的具有依附性。而在享用这种依附性时,她们只能使用一些仪式策略和策略仪式,力求在受宠期间的私己利益达到象征性普遍化,或象征性地占有正式利益。而正式权力的竞争仅限于上层男性,女性只能竞争一种必然是“半正式的权力”。[36]女性即使握有实际权力——多半与婚姻或情爱关系有关,那也必须将正式的权力显示留给男人时才能完全行使这一权力:她们若要拥有某种权力,就必须同意只拥有灰衣主教式的半正式权力,亦即受支配的权力,该权力只能托庇于一种正式的权力,通过代理人来行使,以致于仍然服务于它借用的权力。[37]这亦在法国1804年公布并长期施用的《拿破仑法典》中可以得到证明,经济上不独立的女性,即便身处再高的社会阶层,在婚前也是受父亲监护的,婚后即便有丰厚的嫁妆,某种意义上也仍是丈夫的一种象征性动产,在法律地位上如同未成年人,均无权处置自己的收入。[38]
性别秩序赋予家庭中丈夫和家族中父亲以绝对优越的地位。在理论上,情妇们的消费只能以“越位”与“代偿”形式等同于国王与贵族男性本身的消费,并且成为男性支付能力的表征,而并不真的属于女性自身。
因此,奢侈消费与其说是女性风格的胜利,而根源依旧属于男性的胜利。
于是,便不奇怪左拉笔下的主人公慕雷以男性特有的狂妄与自信戏言道:“巴黎不是属于女人的吗?而女人不是属于我们的吗?”[39]
然而,我们并不需要将自己困囿于对桑巴特思想的批判活动中,也许,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全然的涵盖资本主义起源的一切因素。在桑巴特的分析中,一种原本被遮蔽的社会体系渐进浮现,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非线性”的厚度与维度,特别是他看到了女性化风尚在历史中的涌动,进而将性别关系与性价值观的迁变重新纳入历史,桑巴特的独创与别致,特别是他随笔主义式的流畅,不致使人陷入繁复晦涩的文字迷障。对于那些致力于社会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物质文化与性别、阶层关系的研究者而言,在固有的知识场域内,我们或许需要对历史上隐蔽因素的再审视。
参考文献&注释:
[1]参见[法]左拉.《妇女乐园》[M].侍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第273 页.
[2]亦称之为“德国历史学派”(The school of German history),其先驱为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以萨维尼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政治学方面,初步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继之则为我们较为熟悉的马克斯·韦伯与维尔纳·桑巴特等。
[3][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4]但有学者认为,桑巴特与韦伯在溯源宗教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形成的独特作用这一方面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的同时,对于资本主义精神迥然又具有本质同源性的阐释。参见[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智强等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3月,第493页.
[5]马克斯·韦伯考察了亚洲与印度的社会宗教,由此得出,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抑制性特征。
[6]韦伯对新教伦理作为一种对于民族性格的影响,对资本主义为何发生在西方而非亚洲与印度等地区做了对照性的考察,亚洲的宗教与文化观念对于资本主义伦理的抑制性特征,因而排除了在亚洲与印度以及其它地区产生资本主义要素的可能性,进一步为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原因提供一种可靠的参照与控制形式。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沈海霞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年.
[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沈海霞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
[8]参见[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葛智强等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3月,第482页.
[9][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10][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11][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12]当时的巴黎存在大量不事生产的人,而他们的收入来源则基本上是为王公贵族提供服务。此处参见[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13]桑巴特认为,个人的奢侈是非生产性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奢侈的客观化,集体的奢侈则倾向于一种生产性。
[14]桑巴特枚举了大量文学与艺术领域的主题变迁来作为情爱回归,肉欲解放的证据,诸如他提到了马萨乔、吉尔贝蒂、波提切利、提香等艺术家,以及博亚尔多,波利齐亚诺、阿里奥斯托等等以女性与情爱为创作主题的诗人。参见参见[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65页.
[15]在桑巴特看来,这可以与同时代欧洲上层社会中引诱、通奸与卖淫现象的猛增来得到证明。参见[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16][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17][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M].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第66页.
[18]这些名称包括宫廷情妇、宫娥、情人,其中并不排除一些与贵族发生的合法的纯真恋爱关系,于是对“情妇”的所指意义更为准确的界定为“如若一位女性与显贵人士的关系超出了纯粹的智力服务,那么她自然可能是一名情妇。”这个阶层在非法情爱的普及成为世风之后也出现了分化,这表现在对于性关系的态度上——以“用金钱是否可以买来一位女性的爱”来度量去区隔情妇与妓女。参见[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19]洛可可风格:这一风格起源于法语“rocaille”,原指一种以贝壳与其他石雕饰品的装饰风格,18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部分地域,在“洛可可”一词最初被用以命名一种包罗艺术、服饰以及室内装饰风格时,其涵义更倾向于贬义,因其形式的纤巧与华丽,迥然于古典主义的严肃,且因其与宫廷贵族女性奢靡与轻佻的作风紧密相连而具有秾丽的享乐主义的色彩。
[20][荷]L.S.梅西耶.《巴黎写真》(Tableaude Paris.Amsterdam.1783)[M].第一卷.1783-1788:p22
[21][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22]相关研究可以参考[美]戴维·孔兹.《时尚与恋物主义:紧身褡、束腰术及其他体形塑造法》[M].珍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23][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24]如果尝试将桑巴特的观点作更为准确性的概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是奢侈品所需的精制与分工促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25]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册)》[M].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第608页.
[26]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5页.
[27]同上。
[28][奥]斯蒂芬·茨威格.《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传》[M].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4月.第5-25页.
[29]同上。
[30][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3页.
[3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32][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33]同上。
[34][美]托斯丹·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第45 页.
[35]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册)》[M].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第301页.
[36]男性主宰全部社会秩序,拥有全部正式制度,首先是神话—仪式和系谱结构,这些结构把正式和私己之间的对立归结为外与内,因而也就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立,由此建立起一种系统的等级化体系,将女性的作用规定为不体面的、私下的、至多是半正式的存在。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感》.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37][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感》.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38]参见《拿破仑法典》[M].李浩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10月.第50-52页.第二节,监护.第389条—第392条.
[39][法]左拉.《妇女乐园》[M].侍桁,译.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第2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