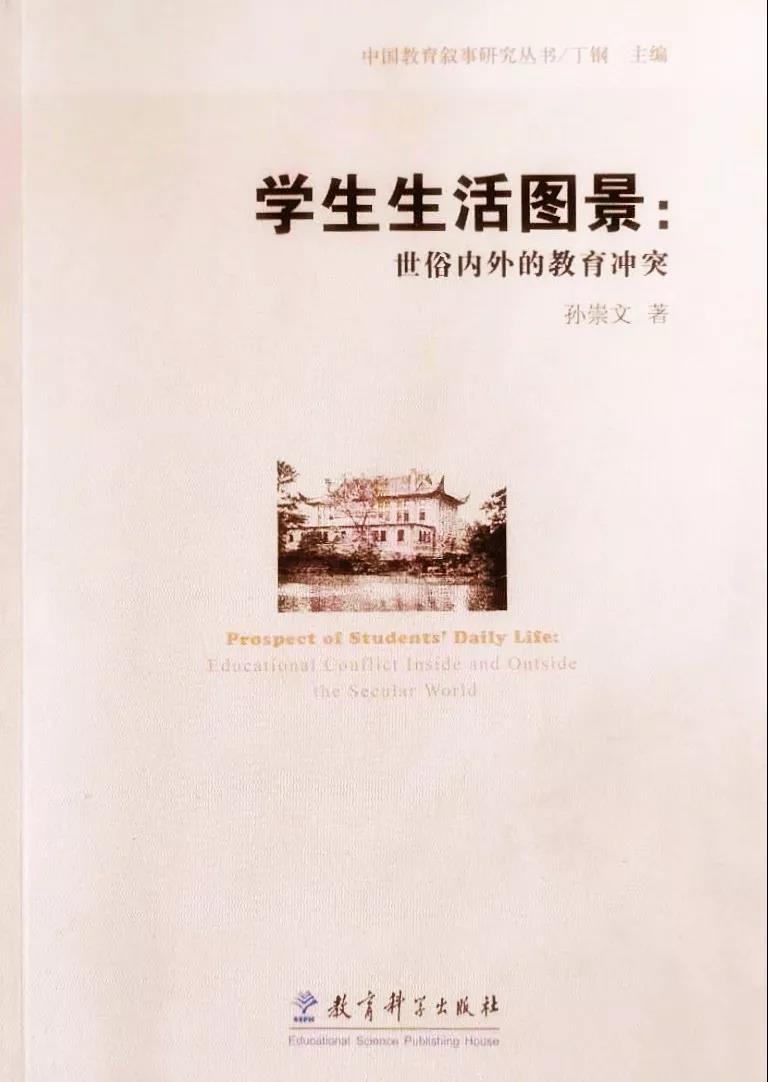
《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
孙崇文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摘要: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闭锁的国门,也由此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与屈辱的一页。基督教随即乘虚而入。基督教教育及随后出现的基督教大学最初不过是传教士手中用来开拓地上的“上帝之国”的“精神狩猎”的工具而已。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是相当地吊诡,基督教大学并没有完全按照预先设定的轨迹前行,最终竟成了“无信仰的中心”,“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教育需求,尤其教育的世俗化和工技化要求,在规定和控制着”基督教大学发展的实际进程。作者试图通过对基督教大学生各个侧面地生活图景的“重构”,来驱散历史的雾霭。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第5章第3节部分(文字略有删节)。
“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1]。这是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们留给外籍人士的印象,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标准画像。而参与体育这“劳力”的活动实在有失体面和尊严,是传统士子们所不屑为的粗俗与野蛮的行为。然而,这种观念在基督教大学却受到了彻底的颠覆。基督教大学要培养“阳刚型”基督教徒,鼓励学生运动,引进了多种体育项目,并开出了体育课程,流风所被,对传统中国社会也起到了移风易俗的功效。而现代音乐和戏剧,也得以流布中国。
(一)
体育健身
基督教大学的开办者们信奉的是“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所以极为关注学生的身体锻炼,并将其视为培养“阳刚型”基督教徒的不二法门。圣约翰大学,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诞生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同时也是我国近代体育事业发展的摇篮和温床,许多近代体育项目正是由圣约翰大学引入中国,领风气之先,并由此提供一种样板而逐渐影响和推广到其它学校和地区的。据统计,由圣约翰大学正式引进我国的近代竞技体育项目共计18项[2]。
圣约翰大学成立伊始,学校就按照西方教育模式的要求在学生中提倡开展体育活动。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起初学生们也是“每不喜脱去长袍,从事竞走”。所以,学校“不得不采用强迫制度,规定运动时间”[3]。徐善祥清楚地记得,学校规定学生每天必须有两个固定的时间段用于身体锻炼:上午是集体的早锻炼,七点钟全体学生都要到操场“做半小时的集体哑铃体操”;下午4点钟下课以后,则是学生的自由活动时间,学生们大多在操场上自由运动,而“凡遇星期一、三、五下午4时半至5时半,群至操场参加军式操演(天雨则免)”[4]。起初,学校体育设施不甚完备,下午体育锻炼也是“一任学生自由,踢毽子、跳绳索,放纸鸢,皆通常之游戏”[5]。稍后,学校开始规定下午活动的体育项目,一个是从博习书院(东吴大学前身)学来的“捉人”游戏,一个是美籍教师引进的“圆场棒球游戏”。以后,又逐渐引进了田径、网球和足球等项目。1890年,学校举行了第一届田径运动会,这也是上海华人社会举行近代体育比赛的第一次,竞赛的项目包括短距赛跑、套麻袋赛跑、跨栏、跳高和拔河等。从此,学校于春秋两季每年各举行两次校内运动会。

图一 上海圣约翰学院学生拖着长辫子在跳高比赛中
集体体操或“军式操演”则是一种强制性的运动,其目的在当时主要是为了“矫正姿势”,进行一种纪律教育和服从训练。起初,“军式操演”也仅被学校当作“户外运动之一种而已”,但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学校在顾斐德教师的带领下成立了学生军,开展军事训练,并将其作为必修课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每周两课时,从而使圣约翰大学也成为中国最早开设体育课程的近代教育机构(1921年之后,圣约翰大学更在全校范围内实行了“二年强迫运动制度”,将体育列为必修课,规定一、二年级学生必须参加)。

图二 圣约翰学院学生军
“军式操演”严格按照美国陆军条例执行,学生们被要求严格执行,绝对服从上级的指挥,违者将毫不犹豫地处到处罚,如果学生在一年之内受到50分的扣分处罚将自动离校。马约翰甚至曾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就因为在训练中“模仿了一下队长做指挥的样子,立刻就被校长开除出校”[6]。圣约翰大学的“军式操演”是动真格的,起初学生们训练时使用竹杖,1898年由萨镇冰提督介绍学校收到了两江总督赠送的200支训练用旧式后膛枪,至此学生们使用真枪训练。在每年的毕业典礼上,圣约翰大学都要举行一次阅兵仪式,学生们纪律谨严,步伐一致,一身戎装,手持真枪,赢得中外来宾的交口称赞,其它基督教大学“亦多从而仿效之”。在圣约翰大学成立学生军的影响下,20世纪初年东吴大学也组建了一支编制为一个营(下辖4个连)的学生军。
1895年,是圣约翰学院学校体育得到发展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学校来了几位来自檀香山的华侨学生,他们酷爱体育,也把不少体育项目带来了中国。他们对体育的热情也逐渐感染了圣约翰大学的其它学生,并最终推动了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并逐渐将体育活动的影响逐渐推广到校外。在它的影响下,上海南洋公学(即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中西书院等学校的体育活动也逐渐开展起来。1904年,圣约翰大学联合上海南洋公学、中西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成立了大学体育联合会,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在四校之间举行一次运动会,项目以田径为主。1914年之后,在大学体育联合会的基础上又相继吸纳了金陵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和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组成了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每年都要组织成员学校学生参加比赛。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一直是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体育赛事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各项锦标的有力争夺者。
二十世纪前二十年,是圣约翰大学竞技体育成绩和竞技体育人才的高产期。学校采取了各种奖励措施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和比赛,各种项目的体育运动队组织在圣约翰大学纷纷成立,其田径、足球、网球、棒球、篮球、排球和羽毛球等项目成绩最优。田径方面,1890年的校内运动会开中国学校田径比赛之先河;1911年,第一届中国运动会上,圣约翰大学排名学校组第一;1913年,5名圣约翰大学生代表中出征马尼拉第一届远东运动会,结果26名中国选手仅获36分,而5名圣约翰大学学生就获得了26分;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又有6名圣约翰大学学生代表中国出征,结果收获了三枚银牌。1914到1925年期间,在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主办的5个主要项目的比赛——12届田径运动会和足球锦标赛、9届网球锦标赛、8届篮球锦标赛、6届棒球锦标赛中,圣约翰大学共赢得了47次冠军中的20次和1次并列冠军。
成立于1901年的圣约翰学院足球队和成立于1902年的南洋大学足球队是沪上足坛两支最负盛名的劲旅,两队自1902年开始正式交手之后就此订下了年度一赛的成例。

图三 1902年圣约翰大学足球队
1914年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成立后,圣约翰大学和南洋大学的足球比赛依旧是该联合会所有比赛中的最大看点。与其它球类比赛采用单循环制不同,唯有圣约翰大学和南洋大学两校的足球比赛采取三赛两胜制,规定两校互值主场一次,若两队一胜一负或两平则移师中立球场作第三次决赛。当时,上海合格的中立足球场只有麦根路(今淮安路)上的铁路职工球场。由于球场离两校较远,决赛时铁路局还为两校师生特地开出了专车,由南洋大学所在的徐家汇站发出,驶经梵王渡圣约翰大学校址直达麦根路球场。圣约翰大学和南洋大学的足球比赛历来火爆,赛前双方都要举行誓师仪式,会上校长亲自讲话,然后是校友会代表、拉拉队代表相继致词,最后和着台下同学们齐整的校歌运动员宣誓一定要拿下对方。比赛时,场内更是旗幡招展、军乐嘹亮、锣鼓震天,鞭炮齐鸣,煞是热闹;而球员们在场上更是你争我抢,不甘示弱,拼得火药味十足。1902年升入圣约翰大学的余日章,也是学校足球队的队员,正是在一场与南洋公学的校际足球比赛中不幸负伤,结果高烧数周不退还为此几乎失去了一条右腿。可见两校足球比赛之激烈。随着比赛的跌宕起伏和场上队员们的激烈拼争,比赛双方拉拉队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有的时候,“胜利一方的欢呼和威力传播甚远,而且转成对败者的嘲弄,终于导致了一场两校学生之间的斗殴。胜利队处于巨大的危险当中,不得不招来警察护送他们出校”[7]。所以,被用来当作两校决赛球场的麦根路球场会被当时的球迷们唤作“古战场”。两校之间的比赛甚至也吸引了众多市民的驻足关注,成为当时上海滩上的一桩大事。比赛时“观众动辄万千,学校邻近,倾巷以赴……其情况无逊于裕佛节之静安寺庙会”。1919年12月13日在圣约翰大学校内足球场举行的两队头场比赛,就吸引了“中外男女来宾约有四千余人,唐绍仪同女公子亦在场观看”。为示比赛的公正,双方还特地请来了公共租界的警察长白勒脱当公证人,结果两队各进一球,未分胜负[8]。
竞技体育的发展,关键在于拥有良好的体育氛围和群众基础。自1900年起,参加体育活动的已不仅限于几个体育尖子,而成为全体学生共同的爱好。学校经常组织班级之间的体育比赛,这样每一个班级的学生都“出现了很大的激情。每一位班长都想尽办法去组织他的代表队参加训练,当运动会的日期临近时,整个学校都行动起来了”。比赛的时候,全体教师充当裁判,“所有的家长也都被邀请来看他们的子弟在运动中获胜,当他们在看台看到自己的儿子得胜时,脸上都呈现出一种巨大的骄傲和喜悦”。这样,整个学校都被带动起来了。他们平日里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当时学生们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是网球、足球、垒球和田径[9]。
为了充分满足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需要,这一时期学校的体育运动设施也得到了重点建设和逐步完善。1895年,学校利用钟楼前空地建成了网球场;1897年,建立了第一间简陋的体育室;1900年,在梵王渡租得一块足球场;1909年,在苏州河东岸兴建一座正规足球场,并附有440码煤屑跑道和6道220码直道,可以开展正规的田径和足球训练与比赛;1911年购得吴家宅新校区后,扩大了运动场地;1919年,建成设备齐全的体育馆,该体育馆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办公室、篮球场、可供百人站立的看台,并设有多种由美国制造的可移动的体操器械;下层则是室内游泳池、更衣室、淋浴室、看台、体育用品储藏室、炉子间和池水过滤设施等;至此,圣约翰大学的体育设施渐臻完善。1929年50周年校庆时,学校又建成了一幢交谊室大楼[10]。
1912年入校的林语堂十分庆幸自己能够考入圣约翰大学。在这样一种浓厚的体育氛围中,生性活跃的林语堂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并且还是圣约翰大学校内知名的一把体育好手。他在体育上的兴趣相当广泛,并在多个体育项目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四年学校生涯中,他学会了打网球,参加了学校足球队,还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从夏威夷籍学生根耐斯那里,林语堂学会了打棒球的技术,是一名精于投上弯球和下坠球的垒手。而最让他自得的是曾经创造过一项一英里赛跑的校级纪录。1915年5月15日至22日期间,林语堂甚至还代表中国出席了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的远东第二届运动运动会。虽然,最终他没能赢得锦标,但他知道,要不是考入圣约翰大学的话,即便他在其它任何一所国内高校求学,他是不可能有机会也不可能有意识这样积极地参加体育活动。他感谢圣约翰大学给了自己一个“健康的肺”。

图四 1929年落成的圣约翰大学交谊室大楼
马约翰[11](1882-1966年)更是圣约翰大学贡献给中国体育事业的杰出代表。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自幼丧父,所以求学时间较晚,但从小喜欢运动。1904年,马约翰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就读于医学部, 1911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在圣约翰大学待了整整7个年头,是圣约翰大学体育发展的见证人。他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和游泳代表队的主力,尤其喜爱田径运动,曾多次获得一百码、一百二十码、八百八十码和一英里等项目的冠军。1905年,在上海“万国运动会”上马约翰为学校夺得1英里赛跑冠军;191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他又力拔高校组八百八十码组的头筹。由于出色的体育成绩,1914年马约翰被清华学校聘任,以后一直从事体育教学与研究工作,被誉为是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
(二)
艺术怡神
基督教大学带来的不只是强身健体的体育,还有陶情怡性的艺术。戏剧是这样,音乐也是这样。
丁罗南曾专门研究过中国现代戏剧的起源问题,他的结论是受西方戏剧的影响,中国现代戏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国基督教学校所上演的学生剧,具体地说就是1898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学生上演的《官场丑史》。他说“上海的学生演剧最早是受了欧洲人办的教会学校在圣诞节的恳亲会上演戏娱乐的影响,开始搞起来的”。最早的学生演剧考证下来可能有两则,其中之一就是“汪仲贤(优游)在《我的俳优生活》里讲到的1898年圣约翰学校演出的《官场丑史》”。事实上,欧阳予倩也早就指出,“上海是新剧的发祥地,远在一八九八年就有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学生演出”[12]。
其实,西方戏剧流入中国的时间还可以再往上追溯一段时间。1866年,外国侨民就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座西式剧院──兰心大剧院,它由外国人经营,定期演出业余剧团ADC编演的戏剧。但是,这毕竟还是外国人演外国戏。受西洋戏剧的影响,借鉴西洋戏剧的模式而由中国人独立创作和表演、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戏剧,则与二十世纪前夕基督教学校的学生演剧有着莫大的关联。这一时期学生剧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基于对中国传统剧目不足以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不满,借鉴以对白和动作表情达意的西方戏剧的表现程式来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创出了“时事新戏”这种崭新的戏剧形式。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界公认,为中国早期话剧先驱的正是基督教学校学生所演的时事新剧作。不过,具体考证基督教大学中国学生的戏剧演艺史可能还可以再往上追溯几年,因为今日我们仍能找到圣约翰大学学生1896年时的剧照[13]。

图五 1896年圣约翰学院学生出演“威尼斯商人”时剧照
1898年由圣约翰大学学生创作并演出的时事新剧《官场丑史》,描写一位乡下财主到城里缙绅人家做客,见到豪华场面便不知所措的情形,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大丢其脸。此人回家后立志做官,居然捐得个知县。做官后,虽然他也学得一些官场礼节,怎奈不会断案。后来终被革职,当场将官服剥下,而里面露出的仍旧是乡下人的土布衣衫。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部戏 “既无唱工,又无做工”,没有沿袭传统戏曲的表现方法,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戏剧功夫自成一体远非初登舞台的青年学生所能掌握,相比之下还是西方戏剧那种以对白和动作表情达意的表现手法更容易为青年学生所模仿;但是,戏中一些情节却是从传统戏曲中化用过来的。这一点,即便在以后学生出演的外国故事剧里同样也体现得很是充分。从戏的主题思想来看,则有着明显的讥讽色彩,借着乡下财主之名,人们趁机好好地奚落了一番满清朝廷的闭塞与落伍。
基督教大学学生出演时事新剧,通常名义上是为了颂神或赈灾而举行的义演,但学生剧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强烈地显示出它与“宗教剧”的不同。学生剧很少直接以宣教为目的(当然,不少剧作中也怀有浓厚的基督教情怀[14]),相反基本上沿着两个平行的方向向前发展。一个是模仿着上演一些外国经典戏剧,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就很受基督教大学生的青睐,可以说是常演不衰。最早上演莎士比亚戏剧的依然还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在1902年首先进行了尝试;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倾向就是坚持时事新戏的特点,实际上也戏剧表演也成为基督教大学生们抒发其政治意识和倾向的一种途径。
学生演剧活动,是基督教大学生们比较喜爱的一项活动,事实上在圣约翰大学最初的学生社团中就活跃着一“莎士比亚研究会”,该会每星期六聚会一次,宣读莎氏剧本一种。而燕京大学的学生戏剧表演活动同样非常活跃。除了侧重现代剧表演的海燕剧团、燕剧社等学生戏剧团体外,其“国剧社”和“昆曲社”等更是以继承和发扬国剧艺术为己任,曾上演过全套的《群英会·借东风》、《打渔杀家》和《法门寺》等多本经典传统剧目,在当时颇负盛名。
在燕京大学学生中,该校1923届毕业生谢婉莹是一位十分活跃的戏剧爱好者,她经常组织和参加学生演剧活动,大学五年期间令她记忆犹新的戏剧演出活动就有多次。她记得,结合英语教学,她和同学们一起上演过《威尼斯商人》和《第十二夜》等多部“莎士比亚”的名剧,由于得到了美国女教师们的热心帮助和悉心指导,加上学生的忘我投入,演出获得相当的成功,甚至连鲁迅先生都曾撰文表示赞许。
在她记忆里,还有一次的演出则更为疯狂。燕大女校和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Wellesley College)结成“姐妹学校”后,有一次该校女校长到校访问,忽然指明要看老北京的传统婚礼仪式,学校就让学生自治会安排一次演出以满足她的要求。结果,自治会就让谢婉莹具体负责。凤冠霞帔、靴子、马褂之类的道具很快就借来了,但一个棘手的问题却是几经动员还是没有人愿意扮演新娘。一急之下,谢婉莹只好挺身而上,打趣道:“这又不是真的,只是逢场做戏而已。你们都不当,我也不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就当了!”结果由谢婉莹出演新娘、凌淑浩出演新郎,而由陈克俊和谢兰蕙扮演伴娘。当天晚上,学生们在女校教职员宿舍院里,大大热闹了一阵,又放鞭炮,又奏鼓乐,好不热闹。扮演新人的谢婉莹和凌淑浩还着实磕了不少的头。等到戏“演到坐床撒帐的时候,我和淑浩在帐子里面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急得克俊和兰蕙直捂着我们的嘴!”
不过,最让谢婉莹得意的还要数《青鸟》那出戏。上演那出戏时,谢婉莹过足了编剧、导演和演员的瘾,“剧本是我从英文译的,演员也是我挑的”。为了剧情的需要,谢婉莹甚至还把家里养的长毛“狮子”狗也带上了台,“等到它被放到台上,看见了我,它就高兴得围着我又蹦又跳,引得台下一片笑声”[15]。
谢婉莹着实从戏剧表演中获得了许多乐趣。事实上,戏剧表演带给学生的还有许多。作为一所天主教学校,辅仁大学历来限制很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还限制男女学生的交往,规定女生出席的活动要有修女陪伴。可是学生们却并不甘心就范,特地选择了《少奶奶的扇子》和《殉情》等剧目排演,结果不仅实现了男女生同台竞演,而且还在大庭广众面前轰轰烈烈地恋爱了一番,在过足戏瘾的同时,还顺带着冲决着基督教大学的陈腐教规,做了一次自由的抗争。
学生戏剧活动的开展,不仅熏陶了学生的情感,丰富了学生的生活,而且也使得戏剧表演逐渐从阳春白雪式的曲高和寡变成为普通大众可以自娱自乐的艺术享受,使得戏剧艺术得以走向民间,成为普通市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日常的娱乐形式和生活方式。
西洋音乐同样也是伴随着基督教来到中国的。敦煌莫高窟的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唐朝西洋音乐就已经通过基督教赞美诗的形式流入了中国[16]。以后,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大量传播,以及大批基督教教堂的兴建和基督教宗教仪式的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洋音乐。这时的西洋音乐,主要是依附于宗教仪式的举行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在教堂祈祷时和着管风琴声人们齐声唱起了赞美诗。正因为基督教学校是福音传播的基地,所以基督教学校对于学生的音乐教育颇为重视,在学生中组织起唱诗班,有的还相继开出了音乐课程。可以说,在基督教大学,起初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西洋音乐,也会把吟唱赞美诗作为自己一天里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音乐家中许多人不是出身于基督教徒的家庭,就是直接接受过基督教学校的教育。
随着“兵式操练”的引进和学生军的组建,基督教大学的学生们也开始不是通过教堂和宗教仪式来接触世俗化的西洋音乐了,他们在军事训练过程中接触到了“军乐”。军乐在二十世纪相当普遍地流传于基督教学校并进而推广到其他公私立学校。基督教大学成为人们接触西洋音乐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中,上海沪江大学的音乐教育在当时就非常出名。
沪江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的音乐教育,由安德生博士(Dr. Elam Anderson)主持,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修完音乐101课程,这成为学生毕业的一个基本前提。在沪江,学校每个月都要至少举行一至两次的音乐会,安德生博士经常邀请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到校演唱。黄浦江畔的学校音乐室也成为沪江的一景,随时走过都能听到窗后飘来的悠扬的琴声,往往令人驻足凝神。
1928年,沪江大学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音乐会,在社会上一时形成轰动。正是在这场音乐会上,赵梅伯应邀出演,结果他的音乐天赋展露无疑,受到了交口的称赞。女作家苏雪林在初次聆听赵梅伯的独唱后陶醉不已,曾留下这样过一段动人的文字:
“在一阵狂热的掌声中,赵先生的法身涌现于台上。我那时才算认识了这个大名鼎鼎的歌者,原来是这样一个英俊青年,在以前我的想象里,我原猜想他是一个四十岁以上富有人生经验的人呢?那晚他独唱了一个曲子,我不知道曲中叙些什么,但觉得其音调之美,异常动心悦耳,其轻淡处如夏夜之梦,如烟如雾的摇曳于银色月光中;清远处如长天冥冥孤鸿夜飞,拖哀声而没于寥寥了,哀曼处如春闺怨女独诉哀情,甜美处如红窗情侣喃喃细语,深幽处如灵魂中的密语,如秋夜闪烁于天空的星儿;雄壮处如壮士赴敌,如雄狮忽吼,如海涛击石,如大风摇撼千年的巨橡”。
这个能让“不懂歌”的苏雪林女士也陶醉其中,“好像被送入一个别的世界去的”赵梅伯正是原沪江大学的学生。赵梅伯(1905~),早年名章伦,号梅伯,后一直以号为名。祖籍浙江奉化人,父亲赵筱山是圣约翰书院的早期学生,平生喜欢音乐,这对赵梅伯影响很大,中学阶段他也参加了学校的唱诗班,其音乐方面的才赋开始崭露头角。1921年,赵梅伯考上了沪江大学,因其在音乐上小有名声而被指为新生代表在入学的第一个“新生之夜”登台独唱,可惜由于过于紧张而在台上跌了一跤,也因为这样使全校师生都知道了这个“跌跤的赵梅伯”。入学以后,喜爱运动的赵梅伯一度想竞争学校运动代表队,但最终没能如愿,这使他转而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之中。他参加了学校的歌咏团,那里人才济济,赵梅伯开始并不怎么特别出挑,但安德生博士“极赏识他的声音,说他将来很有造就。果然,赵君由歌咏团而八人合唱,而四人合唱,以至独唱一步步的上升了”。成功缘于刻苦,下午放学后别人打球去玩乐的时候,赵梅伯总是一个人留在大礼堂每天都要练上两小时,唱着“丽歌栗土”歌剧中“难测妇人心”的咏叹调。平日里只要一找着机会他都会唱上几句,总是曲不离口,因而也有人略带讥讽地称他为“卡鲁梭”,他也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沉浸在他的音乐王国里。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兼任附中的音乐教师了。一次,英国歌剧明星赫伯特·凯夫(HerbertCave)来沪巡演,安德生博士介绍他与之相识,得到对方的鼓励,赵梅伯更是抓住凯夫在沪逗留短短数日的机会当面请教了几次,从而使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又上了一个档次,知道今是昨非,甚至认为自己以前是在shouting而不是在singing,更下定了以音乐为业的决心。这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几番争执之后见劝阻无望一怒之下父亲甚至中止了对他的学费资助。为了能够继续学习音乐,赵梅伯不得不中途辍学,但他始终未曾放弃对音乐的追求,为投名师他甘愿来回奔波于沪杭之间,把收入的大部分钱都“花在音乐学费、买乐谱,赴音乐会上(仅用少数的钱作生活费),坐三等电车,必要时连黄包车费用”。经过一番独自的摸索,赵梅伯终于找到了音乐的真谛的。1929年,赵梅伯更是通过中比庚款考试取得了留学比利时皇家音乐院的机会[17]。
谈到赵梅伯,不能不令人联想起另一位艺术的追求者陈大悲。陈大悲(1887~1944),出生于浙江杭县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08年考入东吴大学。与赵梅伯一样,求学期间的陈大悲也发狂似地迷恋上了艺术,不过不是西洋音乐而是“文明戏”,他经常参加校内的演出活动,结果也引起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为了能够坚持自己的艺术道路,陈大悲同样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于1911年宣布与家庭脱离关系,并中止学业离开了东吴大学,从此走上了职业戏剧家的生涯[18]。
赵梅伯、陈大悲两人的艺术道路,是他们以牺牲亲情为代价坚持下来的。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投身艺术在当时并不为社会主流所认同,赵梅伯的选择就曾被人视为一种自寻烦恼的“愚人”行为。所以,尽管赵梅伯起初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般爱好音乐的朋友,有几位也想去开辟洪流,但为了环境的限制和生活的压迫,终于一个个的临阵脱逃了,独有赵君却能在那种恶劣的气氛中,去开径自行”[19]。令人扼腕的是,赵梅伯的选择竟然还会受到来自他那身为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且又喜爱音乐的父亲的反对,为了逼他就范父亲甚至不惜中止对他的学业资助。
注释
[1] 转引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50页。
[2] 黎宝俊:“圣约翰大学体育史略”,载《体坛先锋》(即《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177页。
[3] “圣约翰大学运动概况”,《圣约翰大学1879-1929》(五十周年刊),第43页。
[4] 徐善祥:“‘约大’的回忆”,第11页。
[5] 《圣约翰大学1879-1929》(五十周年刊),第5页。
[6] 马约翰:“谈谈我的体育生涯”,载鲁牧主编:《体育界的一面旗帜:马约翰教授》,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7] 马约翰:“谈谈我的体育生涯”,第142-143页。
[8]《申报》1919年12月14日。
[9] 马约翰:“谈谈我的体育生涯”,第137-140页。
[10] 黎宝俊:“圣约翰大学体育史略”,第169-170页。
[11] 马约翰的传记资料所见不多,主要可参阅其“谈谈我的体育生涯”一文,其它资料包括:鲁牧主编的《体育界的一面旗帜:马约翰教授》(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黄延复主编的《马约翰体育言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傅浩坚编着的《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传奇人物马约翰》(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12] 上述引文分别见丁罗南:《中国话剧学习外国戏剧的历史经验》(上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第91-107页)和欧阳予倩:“谈文明戏”,均转引自王列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9页。
[13]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第16页。
[14] 参见王列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5] 冰心:《我的大学生涯》,《冰心全集》第7卷,第646—655页。
[16] 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17] 参见赵雍生:《现代中国音乐先驱》,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版。
[18] 韩日新:“陈大悲传略”,载韩日新主编:《陈大悲研究资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19] 参见赵雍生:《现代中国音乐先驱》,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版,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