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齐格蒙特·鲍曼著. 流动的现代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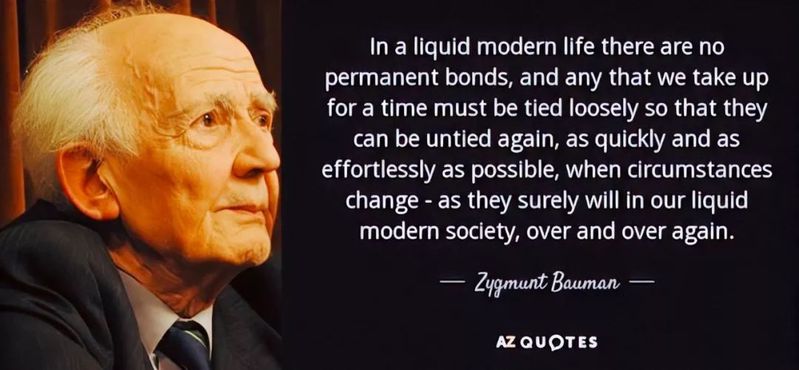
1925年11月,齐格蒙特·鲍曼出生在波兰西部的波斯南省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那时的鲍曼,还不知道自己一生的半数时光都无法安定于一处。
1939年,纳粹入侵,鲍曼一家逃亡到苏联。鲍曼为波兰英勇作战,又为苏联扫除不安全因素,后却因父提出移民问题而被解雇。在这期间,他的身份从纳粹的受害者转向了忠诚的共产党人,而世界事件的萦绕又使鲍曼的学术热情从物理转向了社会学。1968年,在完成学业的华沙大学讲学二十载后,鲍曼第二次成为难民,反犹太清洗迫使他逃亡以色列,又因“不想从一个民族主义的受害者变成另一个民族主义的肇事者”[1],鲍曼一家三年后便匆匆离去。之后,鲍曼在特拉维夫、海法和墨尔本短暂任教, 最终于1971年接受了利兹大学社会学系的邀请,定居英国。
贫困、边缘与逃亡,前半生被排斥与被迫奔波的创伤激发着鲍曼对宽容、公平正义的社会的探索。他关切过去的“大屠杀”与未来或许会发生的“大屠杀”;他关怀全球化下的弱势群体,说道“大象打架的时候, 可怜草吧”;[2]p25他关照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及不安全性之“可怕的三位一体” p298的时代中人们的生活方式、责任与渴望。他是“弱者的冠军”,亦是“对现状的刻薄批评者”。
在鲍曼的60多部著作中, 他探讨了人类状况的永恒方面, 如自由与安全、权力与政治、伦理与道德、身份与融合、焦虑与不确定、爱与恶、希望与怀旧。[3]而出版于2000年的《流动的现代性》,鲍曼关注的是一种永恒的未定状态——“变化”。在连续变化的“流动性”状况下,“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都不能充满自信与确定性地去应对”,由此便导致了不确定性、无知感、无力感与担忧,而这又是“再度携手”、“重新固定化”的必要背景。p12-13在本书中,鲍曼将构架人类状况之宏大正统叙事的旧概念置于 “流动的现代性”之中,思考了“解放”、“个体性”、“时间/空间”、“工作”与“共同体”,试图穿透“虽死犹存”的概念以分析越来越缺乏坚实的模式、框架和机构的“液态”世界。
解放:自由、个体化与公共社会
在第一部分关于“解放”的思考中,鲍曼以对马尔库塞之“抱怨”的评论开始——“很少人希望获得解放,甚至更少人愿意遵照这一愿望办事,并且事实上没有人能确定,‘从社会中获得解放’是以何种方式区别于‘他们所处的现状’的”。p47-48这种心态或因人们实现了某种“想象力不超出实际欲求、想象力和实际欲求都不超出行动能力”p48的均衡下的“自由”所形成。鲍曼区分了“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主观“解放需要”与客观“解放需要”,并由此揭示了一种“感到是自由的东西事实上根本不是自由”的可能性,在这一可能性中,人们因“某种形式的洗脑”而易于满足,实则处于“奴隶状态”的他们“丧失了解放自己的渴望,从而丢弃了使自己变得真正自由的机会”。p49
那么,解放是一件幸事还是一次灾祸?鲍曼总结了两类答案。第一类答案伴随着对“普通平民对自由是否准备就绪”的拷问出现了或“同情”或“蔑视和愤慨”的情绪, p51可谓“哀其无知”或“怒其不愿”。第二类答案认为自由“带来的苦难可能会比幸福更多”,将“社会约束”视为“解放的力量”,强调规则与惯例的价值。p52-55而在流动的现代性的世界,惯例被摧毁、传统被瓦解,“‘个体’已经被当成是他可以梦想、可以希冀的全部自由”p56,“个体”便冲破了社会制度的屏障,其存在与身份不因社会所决定。马尔库塞的抱怨或者说“解放”的口号,已不合时宜。
当今社会,反思性的批评成了我们日常事务的一部分,但这种批评却是“无能为力”的。鲍曼回忆了处于沉重的、固态的、系统性的现代性中的古典批判理论时代,批判理论建立者手握洞察恐惧之刀,力图切断极权主义倾向。而这些批判的诊断对象在21世纪并未消散,对创造性的毁灭和破坏的渴望、对永居人先、永不停止改进的追求,依然存在于20世纪之后。鲍曼接着指出了我们的现代性的形态区别于之前的现代的两个特点:一是相信终极目的的早期错误观念之逐渐瓦解和迅速衰落,二是现代化任务和义务的解除控制和私人化。与此同时,解放的责任和义务已递交给个体——中间层和底层。
在个体化进程中,身份由“承受者”向“责任者”的转型使得人类在“生于何种家”外更要“变成何种人”。“加入”某社会阶层的行动因原初资本差异而不同,且大多数的“占有床位”是对命定位置的确认与适应,风险社会中个体化的尽头并没有“完成”的希望,只是变化床位制造的可成就幻象。进而,鲍曼认为流动的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矛盾即是“在自我独断权和控制社会环境的能力之间裂开的鸿沟” p79(法律意义上的个体与变成实际上的个体的机会之间的鸿沟)。此外,“每日独自面对苦难与抗争”的个体化亦侵蚀和瓦解了公民身份,“良好社会”、“公正社会”与“我”无关。p76
因此,与古典批判理论时代所不同的是,今日之任务是保护正逐渐消失的公共领域而非保护私人在公域中的自主性,需要更多能为别人提供条件并授权别人能力的公共权力,再次将正式的个体化与权力政治联合起来,将现今个体徒劳的奋斗重塑成真正的自主、自我独断与自治。鲍曼呼吁道,解放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液化的社会、个体化的状况使得解放事业出现了新的议事日程——缩小“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裂谷。
个体性:选择、身份认同与消费社会
第二部分是对“个体性”概念展开的探讨。鲍曼以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奥威尔的《1984》之间的争论作为导入,认为二者在世界的终点和目标问题上有着共同的预言,且均勾勒出了悲观性的未来——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的分裂、“芸芸众生不再能对他们的生活负起责任”p105。这亦是鲍曼对流动的现代性的世界的担忧。
之后,鲍曼分析了秩序的内涵、以福特主义模式为代表的“沉重的”资本主义及现代社会,并强调当今“轻灵的资本主义”已背离韦伯的“工具理性”秩序之理想类型与“价值理性”的资本主义。在一个不存在最高权力机关(存在许多互相争夺的权力机关)的情况下,新型的不确定性使得目标选择再次成了主要问题。个体充满可能性的生活在机会中游走、在改变中延伸。太多权威同时存在的“轻灵的、对消费者有利的资本主义”p119迎合、说服和引诱做出选择的人。其中,因个人目标的不确定性而追随或了解他人生活的倾向凸显了榜样-权威的角色关系,寻找建议和指导的个体“上瘾行为”在消费社会中通过选择性的购买强化着“流动性和扩张性的欲望”,而今,“欲望”又被能制造更多刺激物的“希望”所取代。p136
鲍曼认为,消费社会的旗帜是“身体的良好感觉”p138,因而是一种无特定标准的主观体验,它同时使人处在永恒监督所导致的“持续的焦虑和渴望的状态” p140之中,永不满足、永不确定。这便需要购物以“驱除心魔”、变得确定和自信。继而,对消费品的依赖性成为“保持不同自由和‘获得身份’自由的前提条件”p148——“人们通过投降和获得独立性”p149。
最后,鲍曼对不同属类的个体在这一消费社会中的处境进行了剖析。他指出,“生活在一个为富人的利益而设计的相同世界”p156里的穷人越受到诱惑,便越感受到贫困的现实,进而便越能激起对片刻快乐的尝试选择。但由于个体资源的丰富程度制约着选择的范围以及承担错误选择结果的自由,(消费)社会等级末端的弱势群体为降低无趣感的解除束缚行为可能使他们面临着“悲惨、痛苦、苦难,以及永远增长的、破裂的、没有关爱和希望的生活”p158。
时间/空间:短暂、区隔与文明
第三部分是鲍曼对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考察。在对“空间”的讨论中,鲍曼首先以哈泽尔登的“赫里特奇花园”为例,揭示了现代公共空间的严密监控性质及其呈现的“脱离”取代“协商”的都市生活演化方向。
鲍曼指出,当今城市的公共空间背离了“文明空间”的理想类型,其造成的是敬畏和灰心而非美好与生动、鼓励的是消费行动而非人际互动。其中,购物天堂是自我封闭的“献身于无限”之地、纯净无杂质的“我们都一样”之地——这是一种虚构的共同体。鲍曼引用了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应付他者不同性的两种策略,即禁绝策略和吞噬策略:前者通过监禁、流放或屠杀制造空间上的隔离,后者通过容纳、吸收和吞没以终结或消灭他者的差异性。鲍曼认为这两种策略与当今时代的空间类型有所共鸣。鲍曼还借用了“乌有之乡”来说明遵守相同行为暗示方式的令人感到宾至如归的现代公共空间,使用了“虚幻空间”来表达某些城市空间的被认为的无意义性。
探讨了现代公共空间性质特征后,鲍曼尝试挖掘“公共但不文明的地方”背后的人群心态。他认为,人们“谋求同质性的压力”与“消除差异的努力”越有效,其紧张和焦虑便越强烈,便越需要“集体同一性、单调性和重复性的掩护”。p184这使得“公共利益尤其是协商达成的公共利益”更不可信,从而加强了“社会阶层的吸引力”,而后者能够产生地域分离的同质群体防御空间。p185地位集团成为身份认同的第一选择,驱除和分隔的渴望引发了以逃避取代对话的“导致政治病变的公共空间的病变”p189。
在对“时间”的思考中,鲍曼认为“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现代性是时间开始具有历史的时间”p19,并由此考察了时间的历史。时间从“湿件”(有生命的动物的动力和力量)变成了可发明、建造、使用和控制的“硬件”,后者制造了更多差异。时空关系变得“流程性的、不定的和动态的”,“空间是价值而时间却是手段工具”。p194但随着沉重的现代性过渡到轻灵的现代性、硬件时代发展为软件世界,对更大的空间和一致性的时间的追求改头倒尾,空间丧失了其战略价值,时间成为价值获得的手段。时空观亦影响着权力关系——“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最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p205与此同时,资本、劳动与管理也发生了变化。
“液态的现代性”下,“‘短期’已经取代了‘长期’”、持续性被液化至失去价值。p213而这可能预示着文明史的转折,即现在不需要积淀出的持久文明成果。鲍曼忧思道:时间的瞬时性改变了人们共处的形式、参与集体事务的方式,“对持久性表示冷漠并避免持久性的文明”使得过去处理生活事务的习惯失去了作用和意义、对行为后果的责任意识淡漠使得人们得过且过——人类文化、道德纽带依赖的两大支柱(对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信念)消散了。p218
劳动:一曲衰词意难复
第四部分对“劳动”的探讨以分析“发展进步”分析为开端,鲍曼指出,其意义在于“时间站在我们一边”与“我们是‘使事情发生的人’”p224两个信条,而现今时代由于“明显缺乏能够‘推动世界前进’的公众机构”、“公众机构改进世界存在方式的任务不清楚”、“现代社会已经个体化了”等原因导致“发展进步”不再与我们相关,并且是一种生动虚构。p226-229正因改善提高成为私人化的事情,那么“要设计未来,就必须牢牢抓住现在”p229。而被“当成是人的‘自然状况’”p232的“劳动”即是抓住更多现在、衡量个体价值进而能够创造人类总体历史的特性。连续性被抛弃后,由一系列短期目标、可被计算的时间片段组成的生活又使得劳动从秩序建构和控制未来的领域转移到游戏的领域——看重每一步的直接效果并当场消耗。p234
鲍曼接着考察了劳动的历史流变:曾经“劳动-阶级-政治”三位一体的结构带来了巨额国家财富,在劳动成为商品之后生产与交换分离;随着旧秩序破碎,新的工业秩序沉重而来,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福利国家承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矗立着;如今的短期心态使得劳动者与购买劳动者命运间的相互依赖性降低、其结合更为灵活而不确定。
处于流动的现代性中的资本与劳动的纽带变得松弛,利润的主要源泉日益倾向于人的思想而非物质实体,资本更依赖于消费者、劳动影响力减弱,控制管理也强调非组织化,人们被信息统治和遥控着……
在本章关于“延迟”的附论结尾,鲍曼指出,由于“人们从事他们生活事务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环境”在工人形成阶级、工人表达良好社会渴望时便已急剧、迅速地改变。p275或许,部分是因劳动者觉醒的不合时宜、迟于社会变迁,才只能眼睁睁地跟随着劳动流动陷入可怕绝境吧。
共同体:爱恨交织的避难所
鲍曼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思考了“共同体”这一概念。他首先对社群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评述,并认为“所有的共同体都是假定的,是在个体选择之后而非个体选择之前,是计划的东西而非现实的东西。”p281在不确定性的当代,安全感的缺乏使人们“寻找可以确定地永久地归属于它的组织”p283。社群主义者的“共同体”是扩大了的家族式的大家庭,是某人出生于其中的家庭,它同时生产了敌意与不完全的博爱。
鲍曼继而解释了社群主义教条中的或“族群共同体”或“想象而来的共同体”的选择原因。其中,族群共同体的“族群性”有着“吸收历史”、把文化历史表现为“一个特定身份的事实”、把自由表现为“被理解的和被接受的需要”之有利条件p286;并且,民族-国家将民族团结置于所有忠诚之上,压制自觉性共同体、反对地方性,国家发起和监督文化斗争,而这造就了“现今时代共同体唯一的‘成功历史’”p286。
在以上的论述基础上,鲍曼分析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他认为二者谈论的现象相同,二者间的差别实因修辞导致,进而影响了政治实践领域。“爱国主义”赞扬人们的“不结束”和易适应性(可塑性),有着“紧密结合、携手合作”的长期有效的号召,可能激发起“吞噬策略”;“民族主义”不怎么信任选择,强调命中注定的归属,更可能与“禁绝策略”结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区分了“我们”与“他们”,形成了“非此即彼”的情况。共同体的团结,伴随着排斥与净化,而对相似的“我们”的渴望,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的流动性的现代,是无法平息与缓解的。这一共同体或团体是恐怖和焦虑的避难所,它分割了“信任、关爱的区域”与“风险、怀疑以及永久警惕的荒野”。p302
最后,鲍曼讨论了需要公开演示的、具有个体化特征的“衣帽间式共同体”以及打破单调生活场合的“狂欢节式共同体”,二者的后果之一是“有效避免了‘真正的’共同体的凝缩”p328。鲍曼认为“共同体”是“流动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失序的征兆”p328,其产生的“痛苦和不幸”的源泉是个体“可以是”与“实际能是”之间的鸿沟。
反思与怀念
当新世纪的孩童不再观看《西游记》,当各种舞台以价值多元的名义争奇斗艳,当碎片化成为产品和生活的主要形式,当网络信息及其舆论以无形之流控制思想,当消费热望被贩卖为梦想、撑起了财富集团,当虚浮的口号容纳了所有生于此的人却无法激起每个人的行动……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新的习惯、感召、爱与欲不断生成又转眼破碎,我们该如何思考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鲍曼给了我们解答,他以“流动的现代性”为题描摹了这个时代的解放与自由、个体与身份、时间与空间、劳动与价值、共同体与国家及全球化……这些都使得我们对这个时代多一份洞察。同时,他承担起社会学家的责任,考察液态世界下个体努力与局限、关照穷人和劳动者新的境遇,为每个脆弱恐惧的个体无处安放的心与身体找寻失落的公共家园……
在探讨“时间/空间”概念时,鲍曼指出了“流动的现代性”下人类文明及道德伦理方面的困境,这亦是提出了一个当今道德教育的难题。鲁迅曾言“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而现今,或许是“远方和他人”都“与我无关”了。未来的信念、同呼吸的生命,被“瞬时”和“短暂”抽离了的责任感,都已淹没在昨天。个人的奋斗与孤独,在以为的“最好的时代”挥洒热血后顾影凄自怜,俯首对鸿沟,而可能的交响曲的乐章已分崩离析。冷漠,或许是自顾不暇,或许是防御抵抗,又或许是常态。温暖的群体记忆里,还有着相互依偎的习俗、分享担当的意志,它们都在等待朝花夕拾。在打着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之旗帜以凸显个性的时代,坚固的联系、价值和秩序已不复,而除却非连续的“个性”外,我们的空洞之处急需填补。或许,这便是“大难不死”得以留存的几千年传统所能够挽救的……
2017年1月9日,鲍曼离开了他所关心和担忧的世界。在他走前一年,于半岛电视台接受的采访中讲到“我们在营销和广告的包围下长大,到处都是新的诱惑等等,还有全新的时尚。我们认为幸福是连续不断、越来越好的一连串享受。”他引用了歌德所言“幸福在于战胜不幸和困难”、“最糟的噩梦是一长串阳光灿烂的日子,它的另一面不是幸福而是无聊,缺少刺激、缺少追求和奋斗的目标等等”。鲍曼认为这对年轻人是一种警示:不要把你的人生当作一个大礼包,从数不尽的享受中随意采撷而来;把你的人生看做一场漫长的挣扎,当你解决了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往往还有令人非常不快的副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短期悲观、长期乐观。[4]鲍曼对幸福的看法似乎有些“老生常谈”,但或许正因我们可能已经在这个时代的迷离和眼花缭乱中失去了“居敬持志”的心性,所以对“幸福到底是什么”的传统的、苦尽甘来的认识更能使我们“拨云见日”,于“风起云涌”的现代之中清醒地延伸自己漫长的革命,而坚实的美好未来,终将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后绽放。
[1]Bunting, M. (2003). Passion andpessimism. Guardian Review Magazine,5 April.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3/apr/05/society.
[2]Zygmunt Bauman. (2010). Living on BorrowedTime: Conversations with Citlali Rovirosa-Madrazo. Cambridge: Polity Press
[3]Campbell, T., Davis, M., & Palmer, J.(2018). Hidden Paths in Zygmunt Bauman’s Sociology: EditorialIntroduc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5(7–8), 351–374.
[4]半岛电视台. (2016). 齐格蒙·鲍曼:特朗普、难民与我们的恐惧. 30 October. Available at: https://mp.weixin.qq.com/s/uqNPr1gvBCMjdbtYWVcxV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