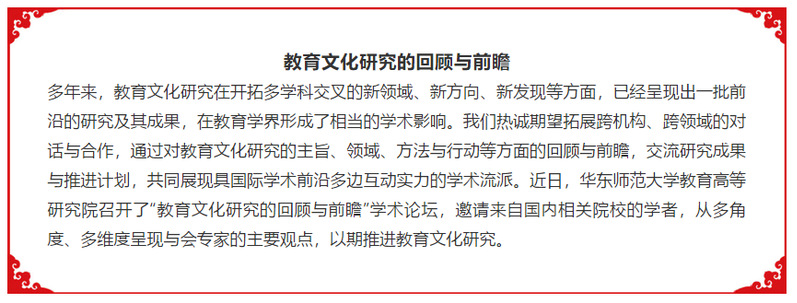
女功:非遗教育中的文化想象
毛毅静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非遗原本是精神层面的文化传承,因为越来越远离当下的文化境遇而遭冷遇。如今整个社会重提尊重传统而不落后的传统,不为回顾而回顾的自我尊重,非遗项目被置于前台,似乎有计划大张旗鼓地来一场文艺复兴。
UNESCO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是随着对世界遗产认识的深化进一步加深的。非物质遗产是来源于民间的创作,是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或传统民间文化)。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以及其他艺术等。因此“非遗”是传统文化的一脉分支,是一种小传统,表征为民众的生活传统和文化传统,是接地气的乡土文化的根基。它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表现形式多与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是活态流变的文化样貌。
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其著作《艺术作为一种经验(Art as Experience)》中曾提出,艺术作为全球化的语言是了解其他文化的最佳窗口。他提倡艺术在增加文化了解与消弭冲突方向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UNESCO 的多项文件也都从政策层面确立了世界遗产对多元文化的尊重,非遗产是促进文化理解的重要载体。从已有的非遗项目的全球策略中发现,艺术以其独特的融合性成为了追求具有全球代表性和平衡性的和平文化的一个组成。因此,通过艺术的手段渗透、融合的教育是极为恰当的教学手段和途径。
本研究中的女功,其实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在描述一个时空关系上的被高度整合的文化。女功首先发源于家的场域,其出现与发展最先是满足一个家庭的生活需要。故也称为女事,旧时指纺绩、缝纫、文绣(刺绣)等居于家庭的多元文化情境。古时传统的“男耕女织”是描述传统民间社会生活图景的概括和缩写,同时这一概括又为上层文化意识形态和观念所认同并加以强化。可以说,上层文化中强势的主流的精致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如伦理道德、礼乐制度、社会风尚等,都自上而下地制约、影响、塑造着女功的形态和特征。作为从中国农耕文明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形态和样式,经过几千年的延续、衍化,已逐步形成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和风貌。这种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技艺发挥至此,早就突破单纯的闺房之乐,成为怀揣令人向往和怀念的人文情怀。现代社会中女功这一传统的手工艺,更是走出内闱,面向消费社会,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研究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从艺术史、民俗的、教育的角度出发,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来构架女性在一个特定社会组织中(如家庭、作坊、市场流通等)借助一定的工具(如织机)所进行的造物活动。主要从女功的功能、人文意蕴、类型、艺术进行解读,并以理论的叙述方式,以大量真实而生动的文本(档案、教材、自传、史料、女性小说等)、图像(教材、照片、录像、作品)与田野调查、访谈、口述等资料直观地呈现和强化这一理论表述。
研究从以下一些方面展开:首先在整体上,以考古发现对女红、女工和女功的历史源流做时代考证,并基于乐府诗(杂歌谣辞)、家庭中的母系生活图景(家计)、《耕织图》等讨论了其通用的原因,在追溯历史基础上将女功相关的知识和内容展开梳证。其次,从分类研究的角度,梳理目前已公布的四批非遗目录,找出与女功相关的内容。以民艺为出发点,从技术文化的角度,以考古出土文物为依据,结合典籍,研究技艺的演变并展开技艺的源流考略。主要聚焦于江南地区历史语境下的女性匠人(婢、作坊中的女性),近现代工艺学校如土山湾画院、工艺传习所、松筠女子职业学校的女功教育。关注女子技术文化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女功教育课程的价值,女子教育与职业之间的两难等一系列女子职业教育的问题。
罗伯特•罗恩菲德(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中认为,复杂社会中存在连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即“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是社会中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书写文化传统;“小传统”是平民百姓口传身授的大众文化传统。从文化的转向来看,女功作为一个典型的小传统样本,从古至今发挥着独特的文化魅力,现时则更多反映了中国现代性的另一面。因此,采用这个视角来叙述的目的,是出于对日常生活的现代性问题的一种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