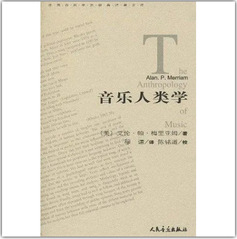文化中的音乐:读《音乐人类学》
文 / 裴祎颖

[美] 艾伦·帕·梅里亚姆 著
穆谦 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0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4831879/
西方对音乐的观念往往都围绕“音乐是什么”这一问题展开。从自然科学出发,音乐是一种人体或物体发出的声音,具有一定的强度与振幅,经过空气传播到人的耳膜,再由耳膜经过神经传递到大脑。这样的定义太过笼统,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音响,包括自然界的声音、人说话的声音、甚至还有噪音等等,显然不能回答音乐是什么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音乐区别于其他声音的种种特征,从构成音乐的物质材料出发,音乐是有规律和周期性的声音,音高、音强、音色和音长有规律的变化组成了旋律、调性、和声、节拍、配器等音乐音响结构与形式。从美学的视角进一步定义,音乐既不是自然客体的标志,也不是概念性符号的载体,而是作为审美对象存在的客体。浪漫主义时期他律论将情感表现视为音乐的本质,将主体的内心世界放在了音乐艺术的第一位,随着浪漫主义音乐的衰弱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自律论认为音乐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情感,提出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1]。进入20世纪,不断涌现的对音乐的新的理解冲击着情感与形式、他律与自律之争,音乐的概念也逐渐走向多元化。
传统的西方文化系统中,音乐被认为是艺术作品,不论是现场演出还是录制成音像,甚至是印刷出版的乐谱,都是审美的对象,音乐的音响体验和形式结构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音乐以成品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供人聆听、由人分析,在吸引一群人的同时,也因其专业性质将另一群人拒之门外。随着殖民将欧洲音乐及人们对其的观念与理解传播到世界,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和音乐也开始受到关注,人们西方的音乐理论体系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西方音乐中心论也开始受到质疑与批评。

梅里亚姆田野调查的部落之一
蒙大拿州西部的弗拉塞德(the flathead)印第安人
音乐人类学早期起源于比较音乐学,在人类音乐起源、音乐历时性的研究方面受单线进化论观念的影响,在音乐文化圈的划分方面受传播论的影响[2],这也就导致它的重点在于“哪里”而不是“怎样”或“为什么”[3],但也有研究开始将目光投向民族语境中的音乐,相对于音乐的结构要素而言,更关注音乐在文化中的作用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体制中的功能。和声、调性、曲式是建构音乐的标准,吟诵、唱腔、击打也是构成音乐的成分;五线谱和工尺谱是记录音乐的符号,口传心授也是音乐传承的方式;乐声或现代音是音乐的介质,所有音乐组合的材料也都只是音乐的载体,而音乐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内容的真正源泉是人及其文化[4],因此对于音乐是什么的定义不能脱离一定文化和社会背景。各种文化音乐所具有的概念,都建立在由个人和各群组以文化来接受的事实基础之上,并与其音乐的声音和态度以及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5]。
梅里亚姆以“文化中的音乐”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观念,提出了对音乐的界定,即“观念、行为、声音”,并对这一界定做出了逻辑解释:音乐的声音是人类行为过程的产物,人类行为过程又是由创造某一特定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决定的[6]。为个人和个人组成的群体所持有、并被他们认可为文化事实的音乐观念,决定着音乐声音以及与之相关的态度和价值观,但概念不能独立产生音乐,它们必须转换成各种行为,才能产生被特定文化认同的音乐[7]。音乐是人的产物,它有它的结构,但它的结构不能脱离产生它的人类行为而独立存在。梅里亚姆列出了在音乐的产生和组织方面的四种主要行为:身体行为、关于乐音的言语行为、音乐的创造者和对音乐有所反映的听众双方的社会行为、以及使音乐家有能力创造出适当音乐的学习行为。
身体行为是产生音乐的前提与基础,正因为人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其感觉、知觉和情感以及心灵世界之间的沟通才成为可能,由此产生的音乐符号和音乐文化才能成为人类表达交流思想情感的特殊中介[8]。如果音乐不能联系自我和他人以及身体感觉,音乐就不具有社会活动的影响,而身体结构相同这一自然基础只是文化理解与交流的前提之一,不同文化中特有的乐器有其特定的操作方式与姿态,不同的唱腔唱法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操纵身体器官,歌唱时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行为也各不相同。
关于乐音的言语行为是对音乐的描述与评价,跨文化交际中常举的一例是,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多种有关“雪”的词语,可见仅自然环境的差别就能带来语词表达上的不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文化语境概念,认为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语言只有在其产生的环境和文化语境中才能被理解。只要存在一种音乐体裁或音乐体系,就必然存在所有人群所持有的某种标准,而这些标准至少有一部分得到了言语表述[9],因此音乐的语词表达行为也是音乐人类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音乐家和听众双方的社会行为既是他们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反应,又是双方对彼此期望的体现。如何定义音乐家的专业性和职业性,他们如何获得音乐家这一角色,有什么职责,其他社会成员对他们有什么期望,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如何?等等问题都是形成音乐行为的重要原因,也都只能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社会中找到答案。音乐家以其特有的社会行为区别于他人的同时,听众也是如此。听众对音乐的反应是音乐家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社会听众对音乐的反应及其行为因当时的场合和他们在其中担任的角色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这也部分决定了音乐家的社会文化意义[10]。
使音乐家有能力创造出适当音乐的学习行为即作曲的习得,作曲的习得是习得的一部分,受制于公众的接受或拒绝,因而它是广泛的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反过来又作用于稳定和变异的过程[11]。音乐被认为是一种动态过程的最终结果,潜在的观念导致实际行为,而实际行为又决定着构造和形态。然而,观念和行为必须被学习,因为文化总体上是一种习得行为,音乐则是人类习得行为的因素之一。当然,要了解为什么一种音乐构造以它现有的方式存在,除了要了解产生它的那种人类行为,还是要了解这种行为的形成过程及原因,以及为产生所需的特定声音组织形式,作为这种行为基础的那些观念是如何被组织,又是为什么这样被组织的[12],而这就需要将音乐置于其所处的文化中进行研究,也就是梅里亚姆所提出的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

非洲音乐
在对文化中的音乐及观念、行为、声音的界定进行阐释后,梅里亚姆在书中最后一部分介绍并分析了音乐人类学的主要课题与成果。首先是对歌词的研究,歌词不是音乐的声音,但它是音乐整体的一部分,与日常使用或书面语言有一定的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就是音乐,因为一般的说话模式要有所改变才能适应音乐的需求,如押韵、元音与辅音的安排、字词的长短与发音等,而通过歌词传递的信息往往也比一般说话更隐蔽且复杂,因为歌曲本身提供了一种自由,使人们可以表达正常语言条件下无法直接述说的想法、观念和意见[13],也使音乐拥有了功能,或成为宣泄情感的方式,或成为揭露社会事实的工具,或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创作歌词的音乐家、演唱歌曲的人、歌曲的听众,所有做出音乐行为的音乐参与者都通过音乐,表现出某种文化所特有的心理问题与过程,也反映了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第二个课题是音乐的用途与功能,音乐人类学不仅仅是对音乐事实的描述,还要探寻音乐的意义。在观察音乐的用途时,研究者试图直接增加自己的事实性知识,而在评定功能时,他试图通过深入理解他研究的现象的意义来间接增加自己的事实性知识[14],音乐的用途是音乐被用于人类社会的方式,贯穿于所有文化层面的音乐活动,而功能则更侧重于以旁观者的视角对音乐为人类做了什么、音乐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进行理解。第三个课题是作为象征行为的音乐,在标示层面,音乐可以是对现实声音的模仿,也可以是对现实的描摹,但音乐的抽象程度之高,使它的性质总是更接近于象征而不是标示,而音乐象征的情感和文化含义在跨文化的层面上不是全然一致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和文化中,音乐在被赋予不同象征含义的同时,也能反映社会文化的其他部分,如性别、亲属关系、社会集团等,甚至也可以象征某种普遍的原则。梅里亚姆接着探讨了美学及各种艺术间的相互关系,他首先澄清跨文化地理解不同社会的审美观不是指以西方的审美评价非西方事物,而需要探寻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持有的审美观念与西方审美观之间的异同,由此会发现有些社会根本没有美学及各种艺术间存在相互关系的观念,也有的社会对此的观念与西方大不相同或极为相似。在音乐与文化史部分,梅里亚姆从考古学的视角阐释了人类如何以音乐为手段来理解文化史,人们过去在民族音乐学中多采用进化论和传播论的各种方法,其基础理论框架在如今看来虽有缺陷,但其潜在的贡献在于我们可以运用统计方法对乐音、乐器和歌词进行精确的分析。最后一个课题是音乐与文化动态,文化既是不断变化的又是稳定的,变迁中总有连续性的线索贯穿于每一种文化,音乐也具有连续性和总体稳定性,音乐的变化在不同文化中也有不同的特点,既包括在时间过程中内部的变化,也包括在文化接触情况下的变异或融合,而同一音乐体系内的不同类型音乐或音乐结构中某些要素的变化程度也多有不同,但音乐构造中往往也总有一些要素成为了普遍因素而保持不变。

音乐人类学家在黑人土居环境中录下的黑人歌唱的Da Lawd歌谱,转引自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15]
将音乐当做艺术作品来分析和欣赏是西方长久以来的观念,随着不同民族的音乐进入大众视野,西方中心主义不断经受挑战,纯粹美学的讨论无法应用于各民族的音乐,由此带来了对音乐概念的再思考,音乐不再是孤立于社会文化的一种声音,人们开始重新看待非西方的音乐体系及其文化价值。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音乐教育中,国际音乐教育协会(ISME)在1967年提出多元的文化背景是时代的必然趋势,一元文化已不再是主流,音乐教育应从多元文化视角出发[15]。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成为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主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音乐出现在中小学的音乐教材中,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景,学生在音乐课程中能够了解到的不再仅仅是西方的或中国的音乐,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音乐及文化也成为了学校音乐教育的一部分。但也不得不思考,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核心是什么?边界在哪里?西方国家实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培养学生对陌生文化的包容和理解,从而消除移民导致的不同民族学生间的文化隔阂,这样的目的在中国似乎不如在西方移民国家那么有说服力。当然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目的更多的是向学生展示并要求学生了解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和音乐,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文化的音乐是否有偏重,如果有偏重,是否就存在某种隐含的立场,如果没有偏重,是不是也就没有了对本民族的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多样性必然意味着差异性,不同文化的音乐的地位是否已事先确定,由此可能带来的比较和价值判断是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想要的吗?
[1]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47
[2]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1
[3] (美)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5
[4]洛秦.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01):50-56+4.
[5]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1
[6] (美)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6
[7] (美)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106
[8]黄汉华.音乐符号行为中的身体间性[J].音乐研究,2009(04):78-85.
[9]- (美)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120
[10]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0-51
[11] (美)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189
[12] (美)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7
[13] (美)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199
[14] (美)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217
[15] 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0
[16] Volk, Terese M .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cultural MusicEducation as Evidenced in the Music Educators Journal,1967-1992[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1993, 41(2):137.
— end —
作者 / 裴祎颖
2019级教育文化与社会专业 硕士生
编辑 / 胡乐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