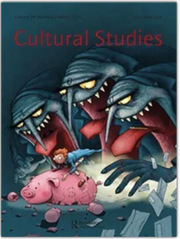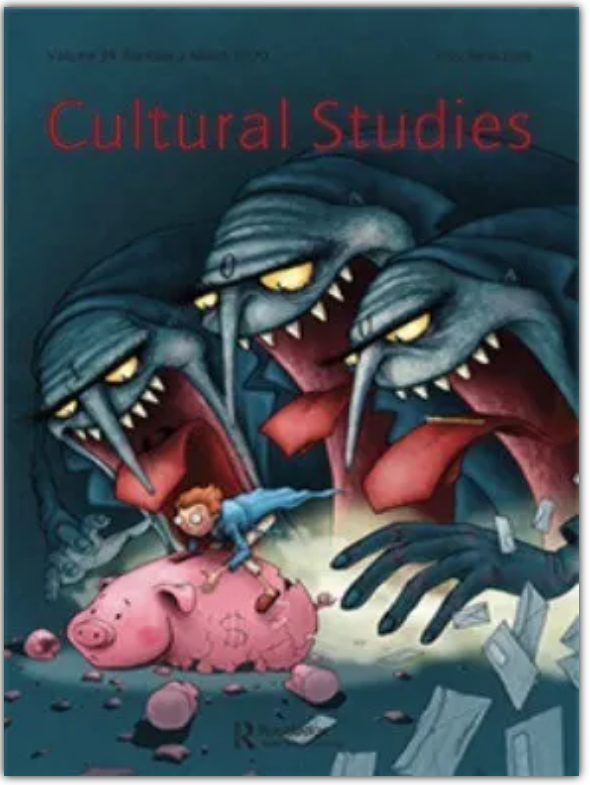
Senno Takumasa
Where are we going now?
Subculture in East Asian cities and the heart of youth
Cultural Studies, 2020,34:2, 208-234.
《Cultural Studies》期刊最近一期的主题是“想象东亚的未来”(Imagining the Future in East Asia),汇集了来自上海、广州、香港、日本和韩国的学者的两类研究——关注当前情况的未来想象和聚焦历史阶段或事件的身份想象。前者从不同的社会语境展开,演绎了亚文化、科幻小说、文化遗产、文学中的青年、港漂等主题下的“矛盾”、“认同”、“绝望”与“希望”。后者则回望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印度间的泛亚主义联结,以及六七十年代香港青年的身份话语。
王晓明和陈清侨于主题介绍中指出,现代竞争和丛林法则的思维使人们短视,继而放弃想象与现实的持续有所不同的“将来”,“我”/“我们”对“他们”观念的敌意促生了精神空间的狭隘与现实的循环。若此种推断是准确的,需首先审视今日对未来的真实思考或假设是怎样的,以及它们是如何被表达和塑造的[1]。本文择取了其中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正去往何处?东亚城市亚文化与青年之心》(Where are we going now? Subculture in East Asian cities and the heart of youth),以展示某种与中国青少年最为相关的文化现象及其投射出的希望困境和教育难题。
在《我们现在正去往何处?东亚城市亚文化与青年之心》一文中,作者Senno Takumasa通过描摹东亚青年文化尤其是文学阅读方面的状况,试图释清当代文化的转变,揭示其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样貌,以及年轻人的现实感受,又透过某些新现象的产生以展望未来东亚社会的包容互通之可能。
借助图像形式,Senno指出,即使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着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但在东亚城市中,年轻人的消费生活和文化喜好却极其相似。这也使得本文对青年亚文化的讨论存在地域间的互证,也是在此语境下,Senno分析了四种主要的相互联系且递进的现象,包括文本阅读倾向、读者与文学的关系、媒体对文学元素聚合的支持、阅读方式对年轻人现实交流和社会问题的映照。
Senno认为,传统文学文化正在转变,不仅涉及文学的边缘化,还有年轻读者阅读品味的变化,即由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演变为新的体裁,如动漫、轻小说(青春小说/校园小说)、BL小说、网络小说等。与此同时,阅读者不再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风格,而是热衷于令人喜爱的角色,如Cosplay和二次创作等同辈群体活动便是此种阅读倾向所衍生的。

Comicup06(Shanghai Comic Market on June2010)
品味之变更进而影响了阅读意图和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在以往阅读纯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会期待通过文本触碰到人性、社会和历史真理,至少会认为理想的好文学是如此。但现今年轻人的阅读旨在于作品中发现与同伴交流的乐趣,他们通过网络和社交圈建立粉丝联结,并对作品角色及世界设定展开热切讨论。Senno在访谈中了解到,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交换信息和谈论作品比追求创作的完美和深度更加重要,因即时的交流可以使他们找到自身位置,获得自我实现感。
读者将喜欢的角色从作品中抽离出来的普遍心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便开始形成,生产者或创作者由此采取商业联动,推销多种与角色有关的媒介,如电影、书籍、漫画、电视节目等。八九十年代以来媒体的发展又将角色中心的阅读方式推向了元素组装(modules)的文学欣赏及创作模式。Senno以手机小说为例,指出这类小说常常是包含了强奸、怀孕、欺凌、毒品、不可治愈的疾病、自杀和真爱等元素的故事模式。至二十一世纪,新的文学体裁如轻小说也被看作是几种元素的联合,同时读者也可以通过掌握模块编织而写出接近自我想象的作品,实现创作梦想,“写得像郭敬明一样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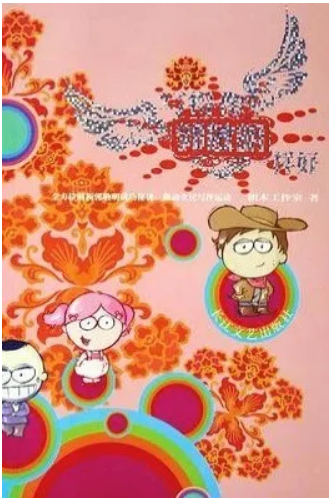
《写得像郭敬明一样好》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
娱乐是年轻人沉浸在动漫、游戏、轻小说、BL小说和同辈群体活动等亚文化形式里的主要目的,而这背后的推动力则是年轻人对当前社会的思考,他们的想法又通过文学和文化反映出来。
Senno指出,三分之一的20-30岁日本年轻人面临找不到稳定工作的压力和失落,“年轻人不知道何时或到底失去了什么,当他们注意到时,他们只感觉他们手上的牌已经被减少了。‘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的话语使他们沉默,许多年轻人被界定为‘一次性劳动力’”。但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感到绝望,2010年的几项调查显示,年轻人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相比1973年提高了,有半数以上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而不是“提升我们个人的生活”。研究者Noritoshi Furuichi认为“有未来潜力或未来有‘希望’的人不会否定自己,即使他们说“我现在不幸福”……当你认为自己将不再幸福时,人们只能回答他们现在的生活很幸福。”Senno在此基础上推断道,当日本青年说他们当前生活满意时,“不是因为对现状感到乐观,而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能够在未来改善现状。”同时,另有一则调查显示,与实现某些目标相比,年轻人在和朋友们相处时更能感到“满足或值得”。Senno认为前人的研究均展示了一个年轻人的形象——他们通过与周围小世界中的朋友寻求联系来克服日常生活,分享障碍感和孤独感。
这类年轻人在文学阅读方面的表现即是注重角色。一是因为他们想参与社会并为社会做贡献,但不知道做什么,且他们生活在被阻碍的境地。他们扮演着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在一个很小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他们寻求一个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试图通过与朋友联系以获得平和。二是源自教室里的“学校等级”(school caste),“每个学生都属于某个群体,并为每个群体命名。他们了解群体间的‘位置差异’”,“若没有分置在小团体中,则无法生活”,也是由此,学生们心有压力,需扮演某种角色、理解自己的身份,以此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这种生活特征造成了学生社会观和生活观的严重问题——九十年代及以后的学校更加两极化,一类是说“如果我尽力而为,我就会成功”的学生,另一类则是“无论做什么,都是无用的”的学生。“出生的天性决定生活”、“生命走向是预先确定的”之意识流行开来,学生认为成功与否是先定的,于是便很难感知到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唯扮演好自己在群体中的日常角色,而这自然而然使他们趋向角色中心阅读。
基于上述现象的分析,Senno认为,“文化变化从未指向光明的现在或未来,但与此同时,我们对克服现代难题有了一线希望”。从东亚的青年文化可以看出,各个地区间的关系是文化共享和互动,而非媒体和政府宣称较多的紧张或冲突。在这其中,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壁垒越来越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和读者,因而广泛的、不相区隔的文化动员是可能的。我们拥有“在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彼此团结的潜力”,而这即是我们面对世界动荡时可以选择的文化道路。但对于年轻人在社会中难以找到希望的困境,Senno未继续探讨。不过,这已经不只在文化的探讨范围之内了。
Senno的研究使用的大多是2010年左右的亚文化素材或社会调查,而随着更为智能的时代的到来与新的媒体形式的出现,近十年东亚地区或许又发生了一些具有共通性的文化变化。Senno的研究着眼于流行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但参与亚文化的主体特征在其分析中是模糊的,他们只有一个标签“youth”,阶层和性别考虑是缺失的,尽管有部分内容提到了学生群体具有等级,但这种等级的标准亦不明确,更多的是为了引出未来理想内涵的两极化,未涉及个体角色、人生期望与阅读品味关系背后可能的社会结构问题,因而Senno尚未释清在这种文化转变实践或新的亚文化形态的生产中,究竟是怎样的青年在投入,又是怎样的青年在放弃对未来的想象。虽然模糊差异会削弱对某种文化/流行现象的真实主体诉求的了解,但的确可以指明一种人人都能够感受到的趋势,并凸显影响大多数青年文化选择和未来想象的社会语境。
亚文化在国内青年研究领域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已有诸多研究揭示了与Senno之探讨相似的青年社会困境及其塑造的消极心态与期望状况,比较典型的是对“丧文化”和“日常迷信”的研究。如有研究者指出“丧文化”反映了当下中国青年群体意义追寻的迷茫与彷徨,自我暴露了一种遵从丛林法则、丧失批判力与行动力、无力将个人与历史联结、陷入自恋主义的“退缩型主体”,他们“为眼前而生活”,“失去了属于源于过去伸向未来的代代相连的一个整体的感觉”;[2]“日常迷信”反映了在严重同质化的媒体叙事、普遍消费化的媒介形象以及高度原子化的市民社会等后工业语境下,青少年群体一面是难以试错、无力改命的窘迫和失语,暴露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被动应对和消极态度,但另一面却是不惜通过投身消费狂潮来实现公共形象的自我确证,日常迷信为青少年提供了“可接受的假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理性人”对未知与恐惧的解释欲望[3]。这些研究印证了Senno的“文化变化从未指向光明的现在或未来”之结论,并描摹了一种中国的青少年形象。

“锦鲤”杨超越
但这种形象的主体是如何被塑造的,他们为何有这样的表达,不仅需要在现实社会中寻求解答,或许还需回到近十年影响最为深刻的新媒体语境,跳出具体的网络参与的亚文化形式,在其建筑土壤上探询。雷启立和梁超群的研究表明,以碎片化、情绪化、非逻辑性、低门槛、短暂的保留和短暂的影响为标志的新媒体,急于在愿景、想法或创意概念与巨大成功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继而破坏了现有的价值和逻辑,如劳动价值被贬抑、道德束缚减弱,它扁平化社会等级,使每个人似乎都看到下一秒钟爬上最高梯级的机会。“善变、浮躁、肤浅和无根的情况正在增加,面对物质的丰富和技术的成熟,我们的文化和情感是苍白的。”[4]此种道德和文化的债务,使得青少年群体只能寄托某种被媒体放大的理想,丧失了未来想象的多样性,与阎云翔指出的问题相似,“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扁平化、单一化,整个社会就一个理想,即成为亿万富翁或者高官。而这一理想无疑追求的是金字塔的顶尖,这意味着最小的可能性成为了所有人的生活理想,结果就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5]
于是,独木桥前半段的“教育”轨迹理所应当地承载了太多人对自身未来的想象,而在某个期望的效果产生之前,尽管有奋斗叙事的神话光环加持,但每个人都陷入对“不确定”的深深焦虑,因为新媒体故事和社会结构事实使得不再有那么多人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就有回报”的美好未来结局了,如“毒鸡汤”和“黑暗童话”的出现。教育是不确定的,尤其对某些群体而言,教育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他们以自己“没有自由和未来的”的心理建构直接转向主动选择被动的命运。[6]
此外,教育欲培养的“真善美”之人,在变动不居的现代,于广义的教育之下遭遇着几种甚至可能相互冲突的教育。换句话说,在思想意识层面,现在的正式教育已无法实现“灌输”,我们无法控制教育空间,无法使我们的教育对象在连接其他社会系统的同时,不造成教育目标实现的减损。“教育”已难以与其他领域一起形成道德或价值观影响的合力,在此种意义上,教育是不确定的,教育的能量和其想要织就的成长线索是不确定的。杜威曾希望的学校与社会建立的联系,现今以网络的形式增强了,人人都可以在“冲浪”中参与社会,但这种大多以非理性形式构成的参与,或许已经背离了杜威对社会责任的强调。
不过,教育之于社会的未来,有一点是极其确定的:“如果知识的目的在于有助于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或抗拒那些其行动会导致一个更坏的世界的力量和个体,那么教育必须找出解决办法。”[7]
[1]WangXiaoming & Stephen C. K. Chan. (2020). Introduction: Imagining the future inEast Asia, Cultural Studies,34:2, 173-184.
[2]刘雅静.(2018).“葛优躺”背后的退缩型主体——“丧文化”解读及其对策.中国青年研究,(04):76-81+27.
[3]刘汉波.(2020).符号赋权、焦虑消费与文化塑造——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日常迷信”.中国青年研究,(01):105-111.
[4]Qili Lei & Chaoqun Liang. (2017). The New Mediaand social culture demoralized and demoralizing in China, Cultural Studies, 31:6, 877-893.
[5]阎云翔.(2013).当代青年是否缺乏理想主义?.文化纵横,(05):56-61.
[6]汪冰冰.(2018).有限的选择空间与想象的未来——对农村青少年做学徒的话语分析.中国青年研究,(12):74-80.
[7](美)杜威著,王承绪等译.(2003).道德教育原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6
— end —
作者 / 朱筠姝
教育文化与社会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
编辑 / 胡乐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