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小说中的女性及其抗议
文/朱筠姝

(美)珍妮斯·A.拉德威 著
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和通俗文学
胡淑陈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为回应美国研究中与读者发展相关的文学理论问题,珍妮斯·拉德威试图通过经验主义的调研,了解和阐释某一文类受众主体的阅读活动意义与其建构的文本意义,并将主题聚焦在她长期关注的浪漫小说类型。这一研究于1984年首次出版,因方法论实践和理论立场的革新与突破被誉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拉德威响应和吸收当时的方法论转向和符号化过程理论观点,开展了“阅读人种志”(ethnographies of reading)研究,具体结合了访谈、开放式讨论和调查问卷,获得了丰富的真实阅读群体信息,“坚定而公平合理地将‘人’(people)重新投入流行文化研究”。[1]她对读者所思所想作出的阐释,始终联系着这一群体的社会文化处境,并借助女权主义理论的解释性学说和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连贯而有说服力地探索了“一套既定的文类规则是如何以及在何处被构建、习得以及使用的问题”(p12),同时又强调意义的复杂性和结论的不确定性。此书出版后即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浪漫小说体裁的文化意义的最好解释”。[2]
本书的基本研究脉络是从浪漫小说盛行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进入主题,主要考察了史密斯顿女性的阅读活动(包括阅读偏好、阅读意义、阅读行为动因或合理化归因)和她们的文本评价与解读(具体指判定“理想”和“失败”作品的标准及解释),最后探究小说的语言和叙述话语及其所诱发的读者现实活动和反应。
在开篇分析了书籍制作、分销、宣传和营销的技术变革对浪漫小说流行的影响后,拉德威便介绍她的研究对象,即史密斯顿的书店店员桃特和她的顾客们,并通过调查说明了这一群体经济宽裕、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多早年已有阅读消遣模式、几乎每日都有阅读等特征。问卷结果显示,她们侧重特定的叙事元素或结构(如感情发展线索、圆满结局等),对优劣小说有着清晰的判断标准(男主角对待女主角的方式),也有着对男女主人公个性品质的偏好(女:才学、幽默、独立等;男:才学、体贴等)。对于史密斯顿女性而言,阅读浪漫小说的意义在于体验不同于日常生活:在使她们脱身于日常问题和责任的紧张状态的同时,又创造了获得情绪愉悦和健康、满足个人需求和渴望的独立时空。浪漫小说实为这群女性提供了一种照顾到个体性、自我感知与呵护心愿的乌托邦式愿景,但阅读结束后她们仍需回到无法改变真实处境的现实,疗愈价值的短效也促使她们重复消费此种文类。(p63-112)

电影The Stepford Wives中的家庭主妇形象
(实被转化为机器人)
阅读浪漫小说这一行为,与史密斯顿女性为妻为母的角色相关。阅读活动发挥的一个主要功能(同时也是阅读动因)是“逃避和释放”,即使她们暂时逃离充斥着沉重责任和义务的环境,并象征性地逃到一个童话世界中,通过女主人公的故事,间接被给予情感上的关怀、呵护和照料,以及个人的价值认同,进而获得支持和完复的力量。在此种意义上,浪漫小说是一种补偿性或替代性的文学,它以乐观的幻想世界构筑了女性对自己和未来的真实的良好感觉。需注意的是,浪漫小说的替代性愉悦可能会消除阅读者对自己生活做出更实质性改变的想法。此外,这些女性可能因在责任中隐身、暂时拒绝牺牲而感到内疚与自责,也可能因阅读活动的时间、花销和阅读文类已有的某种污名受到男性的指责,但她们会启动解释-自责-辩护过程来说明阅读对其自我认知的改变,强调她们“也有权为自己做点事”,建构一种符应文化背景的合理化逻辑。
拉德威认为,这种负疚感的产生与她们所身处的“将工作的地位置于休闲和玩乐之上”的文化环境,以及“女性的身份被与性吸引力联系在一起”但“怯于自由地谈论女性性欲”的文化信息有关,后者可能使她们因现实“无法得到”而转向通过浪漫文学寻找认可的需求,前者又使她们的阅读活动被合情合理地视为“反常和不道德”。因此,这群女性从大众文化尤其是男性所接受的价值观出发,设计了一套为何读浪漫小说的理由:浪漫小说具有“教化价值”,她们可从文本包含的信息中了解既往历史或其他文化的知识或风俗习惯。于是,阅读浪漫小说便可被视为“一种有意义的追求”、“一项有明确目标的工作”、“一种有目的的劳动”。拉德威指出,此种宣称和认知与“坚信教育与成功和地位紧密相连”的中产阶级信念相系,也暗示了“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购买一本平装书”来获得“知识”的进步和民主信念。在这一意义上,浪漫小说也同样具有补偿性,因为阅读活动创造了一种幻象,即通过非正式的方式“获取事实性的‘知识’,达到了取得进步或改变的目的”,间接丰富了这些女性的社会空间,巩固了她们有识而勤勉的自我形象。(p113-154)
本书的四、五章节,拉德威调查了史密斯顿读者群对“理想的”和“失败的”浪漫小说的判定与评价,又在父权制的语境下对其加以分析。调查显示,理想浪漫小说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倾其全部笔墨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唯一且不断发展的恋情(“一女对一男”),而被评为失败的浪漫小说则缺少这一特征。理想的浪漫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开端处于情感孤立和失落境地,之后逐渐建立与他人的联结,其女性自我追寻之旅是由最初抗拒女性特征(通常会有男性特质和举止)到最后重新获得母性的渐进发展史,同时一面保持天真青涩,一面又通过其女性特质(美丽身体和体恤呵护能力)改造男性形象。拉德威认为,这种读者所认同的女性人格发展之路是在父权制文化中建构并得以实现的,强化了女性身份、价值和自我之感,实现了一种“父权制中生养后代这一分工所需要的关系中的自我”。因此,理想的浪漫小说实际认可或确证了整个制度结构的必然性和可取性。并且,女性社会成员在父权制文化中未能获得慈母般的呵护、关爱(她们是照料和关怀的给予者),所以她们会希望在浪漫小说中体验这些需求的满足。如完美的男主人公被读者群认为应该是强健而温柔(温柔特质从隐到显)、具有公共领域影响力的形象,会自冷酷和漠不关心转变为只对女主人公一人忠诚与体贴,其男子气概逐渐符合女性标准。而理想的小说叙事会不断合理化男主人公原初的负面行为,女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学会如何恰当地解读男性,从而恰当地理解在现实婚恋关系中自己所遭遇的事务,并不再希求某些改变。但失败的浪漫小说未能很好地处理男性角色的转变,难以令人信服地缓解或消除女性的恐惧和隐忧,或是为理想的浪漫关系增添了现实性,进而无力提供给女性逃离现实的替代性愉悦与投入浪漫幻想中的振奋、幸福之感。由此,拉德威将浪漫小说视为“测试男性行为和父权制控制之后果的实验性表达”。(p155-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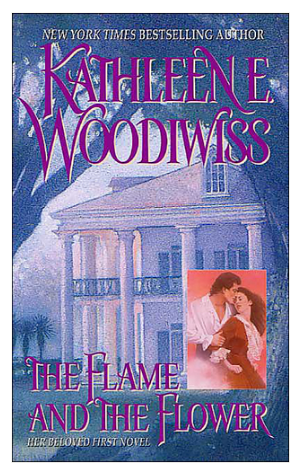
最受史密斯顿女性喜爱的浪漫小说
尾章中拉德威对叙述话语的探讨,旨在了解“关于女性气质的保守观念有多少会在阅读过程中被读者不经意地‘习得’,并在真实世界中被推广为正常、自然的女性发展过程”。拉德威认为,读者对文本的释意策略取决于她们全盘接受的一系列语言和意义相关假定,她们认为语言可准确描述外部真实世界,并赋予语词以此前已被赋予的意义,即她们将现实中的一套原则和规程带入阅读活动中,通过她们精通的文化编码和习俗惯例快速解码浪漫小说的语言结构,但读者本人不会意识到这一事实。所以,每一部作品实际都在重述一个故事,以相同的方式解决同样的事件系列,而读者在参与仪式性重申某个不变神话时,却坚称故事各有不同,深信她们在读另一个未知的故事。这与小说的时间表现方式、冲突制造技巧等叙述策略有关。对于女性而言,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了“所有女性都是独特的个体,她们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但完全有能力活出独特的生命”的幻觉,读者会认为自己在走一条“自由选择的道路”,小说的浪漫结尾其实重申了女性最终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恋人、妻子和母亲等社会或制度角色。
因此,浪漫小说虽具有对女性普遍文化期望的抗争性,控诉了父权制引发的情感后果,也以“反评价”象征性地解决了女性的某些现实需求和女性对男性的某种胜利,但阅读活动却可能化解女性谋求现实改变的冲动,使她们无须变更现状结构便可在幻想世界里得到满足。拉德威指出,浪漫小说的设想根本没有挑战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系,可能只是在休闲和虚构领域完成抗议、转移和遏制真正的对抗情绪,进而保护更加重要的文化场所免受女性的集体质疑及其影响。(p236-263)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者
Nancy Julia Chodorow
有学者评价本书时认为,在拉德威对类型小说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她自己的阐释,而非女性自己言说的产物[3]。这类质疑拉德威在其1991年再版的引言中有所回应,即她支持“呈现即是阐释”的观点,但她若此时写作,也会有一定调整和区分。这一阐释/诠释问题的争论和探讨的启示是:无论是质性资料的组织还是呈现,都可能与研究者本人的知识体系、意识形态立场或偏向,甚至是个人生活史和特殊历史语境相系,研究者的理解可能在经验资料出现的同时即会发生。但我们也不应过分追究诠释和过度诠释的问题,若研究者的解释逻辑合理,且研究对所在领域有一定贡献、结论对读者有启发,那么我们也可如试图理解研究对象真实处境一般,理解研究者探究复杂问题的“诠释性”努力。
如今,距拉德威研究的时段已有三十余年,浪漫小说这一文类本身、读者群体及其体验很可能有了明显的演变,演变过程也可能包孕着真实个体应对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家庭结构等变迁的重要信息。类似的如储卉娟在研究国内网络文学时,便在文本层面上具体分析了浪漫-清穿-种田的类型进化史,体现了个人面对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时解决方案的变化,其中也隐含着对历史的解读和态度,以及对男女权力关系、寻求生活幸福途径的主流认知及其分歧[4] (p155-159)。目光若转到教育领域,想必研究教育小说及其受众体验也会很有意思吧。
参考文献
[1]Jane E. Caputi. (1986). The Library Quarterly:Information, Community, Policy, 56(1), 78-80. Retrieved July 31, 2020, fromwww.jstor.org/stable/4307942
[2]Cawelti, J. (1986). American Journal ofSociology, 91(6),1512-1513. Retrieved July 31, 2020, from www.jstor.org/stable/2779830
[3]Smith, A. (1985). Journal of AmericanStudies, 19(3),471-474. Retrieved August 1, 2020, from www.jstor.org/stable/27554693
[4]储卉娟.(2019).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end -
作者 / 朱筠姝
教育文化与社会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
编辑 / 胡乐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