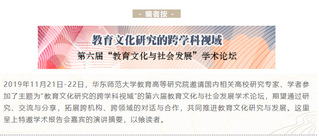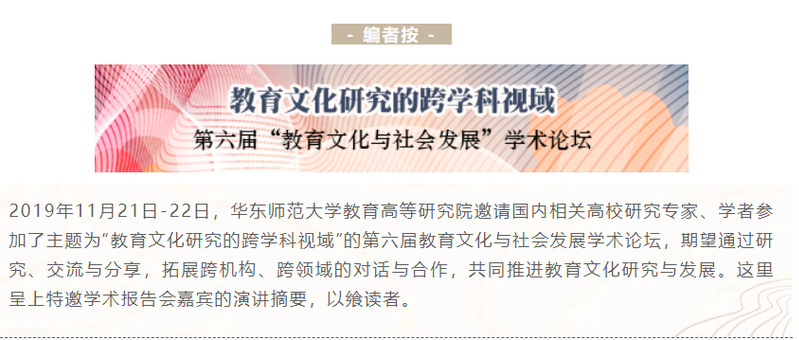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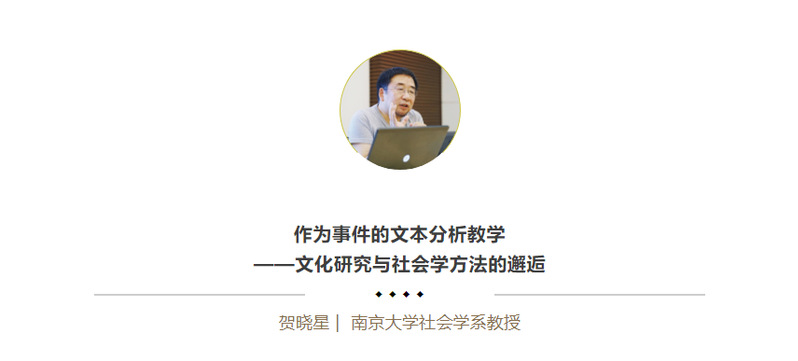
“作为事件的文本分析教学”这个题目最想表达的是:文化研究如何贡献于教育社会学研究?让我们关注一下“事件”一词的方法概念意义。
/一/
“事件”的概念意义
首先,在方法论层面上,“事件”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概念。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试图从人们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之中去把握、描述、分析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
第二,“事件”有其独特的认识论意义。“过程-事件分析”经常被用于个案研究的“本质性个案”分析,对这种个案的研究主要不是因为它代表整体,也不是因为它阐明了一个特征或问题,而是因为它不管多么特殊、多么特殊,个案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理解歌德的以下这段话到底在表达什么。“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由第一种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或典范才有价值。但是第二种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只是到事后才意识到。”(《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1824)
第三,“事件”有其本体论层面的思想。“事件”是现代思想、尤其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20世纪60年代以来,诸多文艺批评的学者,展开了种种有关“事件”的论述。比如福柯认为,对自明性的突破是‘事件化’的首要的理论-政治功能。陶东风老师说,“各种曾经或仍然被我们视作自明的‘普遍’文学观念,实际上最初都是作为一个事件出现的”。厦门大学的贺昌盛老师认为,形而下地讲,“表达成这个样子本身就是一个事件”,“文学事件”就是“语言事件”。做一个类比,上课的“形式”就是“事件”,正如文学表达的形式就是“事件”。我们在这个层面思考教学,有其独特的存在论意义。
从文学“事件”理论的角度说,强调的是“事件=文本”,重要的在于关注“文本”的物性——它的表层(其语言表达的文本特点)。我们说一个文本就是一个事件。但“文本”不是仅指文字组合的一个结构,它可以是一篇教材也可以是一堂课的教学。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事件”理论是在召唤我们从“文本”、“形式”的角度去思考、认识一堂课的教学。让我们简单介绍一堂课“知识、教育与社会控制”,一起来体会一下“教学”的“事件”性。
/ 二 /
教学的“事件”性
相比于《菊与刀》,罗兰·巴特的日本游记《符号帝国》并没有受到文化研究学术视野的应有关注。但是透过现象,巴特确实看到了一些深层的东西。从内容层面上说,巴特从日常生活的极其细微之处,描述了一个能指特立独行的王国——日本。巴特将日本命名为“符号帝国”,重在阐述这样一个充满惊奇的国度,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竟与西方的截然不同。所谓的“符号”,并非是某个所指的表征,而是自身自给自足的、与所指即便拉开了距离也能保持生命鲜活与灵动的某物。因此我将其用于这门课的质性教学中。我用了两个关于“筷子”译文作为教学材料。
一个是孙乃修的译本:
两根筷子结合起来的另外一种功用,就是夹取菜肴的碎块(不象我们用叉子那样去刺);夹取,这个词太硬了一些,太有侵略性(这个词对于狡黠的小姑娘、外科医生、女裁缝、以及有着敏感气质的人来说太不客气了);因为食物从未受到过任何一点比把它夹起来移动时用的力更大的压力;筷子的姿态由于它自身的那种质料——木头或漆——而变得更为轻柔,这里面有一种母性的气质,这种准确、细致、十分小心的动作正是用来抱孩子的那种细心劲儿;这种力量(就这个词的操作意义而言)不再是一种推进力;从这里,我们看到用餐方面的一整套动作;这从厨师所用的长筷子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长筷子的用处不是用餐,而是准备食物:这种用具不用于扎、切、或是割,从不去伤害什么,只是去选取、翻动、移动。
我读了文本,觉得意思很不明了。我认为,译者在一个较浅的层次理解巴特的思想,跑偏到价值判断的方向,因而没有把关键的要点翻译准确。
另一个是怀宇的译本:
夹住,这是一个很重、很刺激人的词(它是爱掐人的少女的用词,是外科医生的用词,是女裁缝们的用词,是易生气的人们的用词);因为,食物从来不能承受大于恰好把它夹起和移动的压力;……筷子的动作因其木质或漆质材料而不显得剧烈,在这动作中,有某种母性的东西,甚至就是在移动一个婴儿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恰如其分的谨慎举动:它是一种力量(从该词的动作意义上讲),而非一种冲动。
比较两个译本中的下划关键词,可以看到,孙的文本有道德价值判断在里头,而后面的相对是客观的描述。“承受”表明食物容易碎掉,一不小心就脆弱,“移动”比“抱”更为谨慎。
西方非常强调能指后面的所指,但是巴特做的是细致地描述所看到的能指。我在课堂上让学生们就这两个文本写读后感。
被我打了“及格”的读后感是这样的:“筷子这种不带强烈侵略性具有母性色彩的功能和东方文化具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东方文化追求的是和平、不强烈、包容,这样的文化背景才使得筷子而非刀叉成为更多与食物联系的工具。”
“良好”是这样的:“他所叙述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异列举,大概是会另只要有一点东方文化底蕴的人所不敢苟同……”为什么打良好?因为社会学首先教复杂性,不能简单地做道德判断。
打“优秀”的则是:“巴特是否和日本有些渊源我不得而知,不过至少在这一文章中总体感觉上令人联想到日本。姑且不论他所引用的俳句,单就筷子而言就令人浮想联翩。中国人也用筷子,不过相较于日本人所使用的则显得庞大而不易灵活操控。筷子的使用过程中不象刀刃一般执着于以直达的方式分解食物的物理结构再以高效率的直线转移到口中,而是顺其自然的随着食物的天然形态,游刃有余地剖析事物,并非放弃于对客体的感知,只是以一种顺应的心情介入其间。咄咄逼人的态势也许更为显赫乃至于眩人耳目,却也失于主我过分膨胀使其所剩无多。”
我读了第二遍大概才读懂。优秀的这个文本中,能指取代所指,成为实质性的表达。表达凸显能指,这难道不是一个带给我们在方法上很多启发的文本吗?
/ 三 /
作为“事件”的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是一个很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一个关键点是,对方到底在讲什么?关于这一点,人类学比社会学更为自然主义,走到极端。人类学认为,深度访谈一定要自然,不能录音,一录音,那个人很可能会紧张。带上笔记本,发明一套速记系统,当场写下来。社会学认为,你那个东西再怎么记,一定是内容,不可能回忆出来怎么讲的情境。人类学认为这不重要,这是因为人类学一般待上几年做调查,对他们的调查而言,看比听重要。但对社会学讲,调查一般不会待几年,待的时间短。录下的东西转录成文本,那么其中的能指,也就是怎么表达的形式非常重要。有学者就认为对方讲的是真是假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讲的,这里头有社会学的意蕴。
因此通过罗兰·巴特的文本,学生们在课堂上遇见了社会学的两种学术走向,然后引起他们心里的动摇,去思考一些平时很少去想的问题,思考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内化掉的东西。
为什么要讲这些?我在东亚教育社会学质性研究工作坊上,也在探讨自己到底想做啥东西。我们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东亚国家,学校教育与研究的意义,也就是强调自己文化的价值,强调亚洲的知识生产。
作为方法的教育社会学,不同于西方教育社会学的东方教育社会学,一种思路是中国研究作为研究内容,比如中国人的面子。我的思路不是以研究对象来定义研究属性的,而是以对表层和书写的关注,凸显中国和亚洲特点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不同于欧美的知识类型。比如书法的价值,最重要的不是书法在表达什么,而是表达本身。全球化时代的东亚意义上的教育社会学质性研究,其一个独特魅力,我认为表现在我们对于文本分析的刻意追求。这并非是说西方的教育社会学者不做文本分析,而是说对于东亚来说,文本不仅是分析对象,文本分析并非仅指去“分析”“文本”,去探求“文本”的“所指”甚至是“能指”,而是同时也可以是一种突显“文本”的“分析”,“文本”成为“分析”的形容词、修饰语,指称着“分析”本身的表达充满了“文本”或曰“能指”的鲜活。
/ end /
整理:陶 阳
编辑:胡乐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