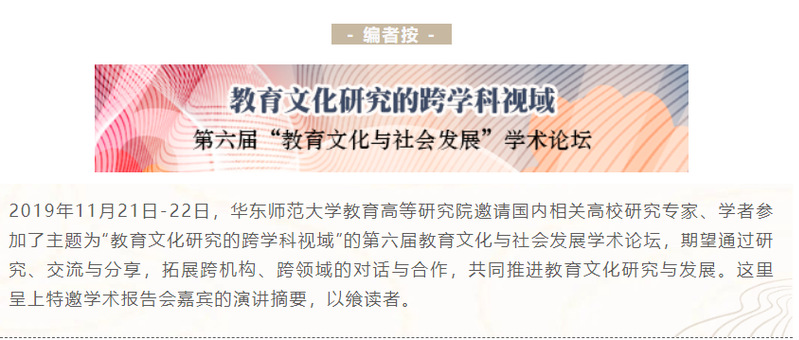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课堂结构与课堂话语方式,很明确的一个主题就是课堂。自从有学校教育以来,教与学的活动就是教育的核心,其内含了教学与发展的永恒主题。当我们讨论教育的时候,就是在讨论教与学,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的状态。因此,我们不会把个人学习行为视作教学活动,因为教学是处理教与学跟发展的问题,人类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人与社会的发展均离不开教育的支撑。
我们称之为学校的地方是一个不断发展延伸的空间。最初的教育活动并没有特定空间,但后来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务,就有了为青年人提供专门教学空间的场所。例如中国远古尧舜时的官学“成均”以及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提出的编班教学。但当今所普及的班级授课制则是夸美纽斯在对中世纪学校中班级授课初步经验进行总结基础上提出的,它顺应了后来的大工业生产的要求。班级授课制可谓近代教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极大提高了教学效率,也有利于大规模培养人才。我们所熟知的班级是一个社会生活空间,一个等级体系,更是一个人际交往的场所,其承载的隐性课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简言之,师生不同力量的关系(规范—角色—互动)及其空间分布构成了课堂的结构。社会学家帕森斯和布迪厄都注意到了班级在个体社会化过程的作用,尤其是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带来了强大的解释力。但是,他们却很少注意学校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持续而累积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有资本的积累和交换,更需要对如何积累进行考察。
课堂生活的实质是一种交往活动,而教学主要是以口头言语和体态语言交流方式展开的。如前所述,教与学是整个教育活动的核心,离开教与学的关系,教育过程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是教与学关系最重要的支撑。韩礼德(2003)认为语言和语法在语篇中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知识/信息的传递和关系的构建。对于课堂而言,还不止如此,语言同时在塑造个体的心智结构(惯习),因此课堂教学中的言语方式就有了第三重目的。刚刚贺晓星教授所讲的文本分析的意义就在于,文本作者以及文本所指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在于读者自身的意义构建。语言和身份是在自我与他人的相遇中构建起来的。在个体内部,个体自身的意义与外部世界的意义之间存在着不断的对话协商。我们可以被外部世界改变;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所处的社会群体改变世界。就词汇语法而言,有些语言类型被认为比其他类型更有价值。在同一种语言中,这些更有价值的类型将构成具有自己语法和发音的标准语言。
具体来看,课堂话语分析有两种基本路径:分别是批评性话语分析(CDA)和民族文化志传统(CA 与MCA)两种方法。CDA倾向于将身份作为意识形态定位的索引或表现, 研究身份的目的是揭示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种方法将微观的语境和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结合起来考查话语者的身份。CA与MCA则不主张事先假定话语或身份的制度性,不考虑超出会话本身的宏观语境,而是将分析限制在上下文的微观语境中,认为身份是在叙述者的故事讲述中构建和施为的,而非先于语言存在的;认为身份是呈现在一定情景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
追溯课堂话语的历史,自然会联想到思想史及教育史上的两位先哲——孔子和苏格拉底。孔子以其“启发式”传世,苏格拉底则以“产婆术”著称。虽然“启发式”和“产婆术”这两种方法被后人看作是相似的,但其实质却是大相径庭。以《论语》为例,孔子与学生的对话大多是其论断式的独白话语,即便记有学生的回应,也大多是附和或简单的应答。同时,孔子在教导学生时常使用祈使句句式,无需主语。例如,《论语》第一篇《学而篇》全部都是语录体。语式的一开始就是“子曰”。每一句话都是对经验、价值、立场的直接陈述, 内容平铺直叙, 不含有任何争辩性,甚至没有语境, 没有叙事, 没有原因, 没有结果, 不是讲述具体事件的话语,而是抽象的语言,只有最后不证自明的真理和结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论语》中的“孔子”本质上不是一个“对话者”,而是一个“教诲者”或“真理传达者”。
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提出了两个概念:“权势(power)量”和“共聚(solidarity)量”,以分析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权势量”指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地位差别的大小,地位高的人“权势量”大。“共聚量”指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地位差距的大小,但是侧重与双方的共同点,即双方在各种社会条件方面有多少共同点。从《论语》的言谈方式可以发现,孔子的权势量很大。所以其对话方式不需要基于假设、前提、证据和推断的论证铺陈过程,而是直接给出结论。
苏格拉底式的课堂话语则与孔子不同。他往往从一个命题(最初假设)开始,然后他接着想:“如果承认了这个,那么必定有什么会随之而来呢?”也就是推出它的后果。苏格拉底问答式有相对固定的程序,学者通常把它分为三步:“第一步称为讽刺,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第二步称定义,在谈话过程中凭借反复诘难和归纳过程,引伸出明确的定义和概念;第三步叫产婆术,引导学生进行思索,得出自己的结论。” 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中助产是关键一步,“助产术”是“帮助对方回忆知识,就像助产婆帮助产妇产出婴儿一样。”苏氏的提问是由浅入深,层层相扣,充满机智和论辩技巧的。诘问的精髓在“启”而非“问”。总体来看,苏格拉底的课堂话语重视“真假之问”与“真善之问”。其诘问法揭示了信念之间的矛盾,从而迫使他人改变某个信条,因为矛盾表明我们某个信念一定是假的。他认为,重要概念之间的矛盾是危险的,矛盾本身构成了人的灵魂的一个缺陷。令人向往的东西(财富、权力等)如果没有正确知识(善)的引导,将走向恶。
对照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对话方式,可以发现这是两种明显不同的教学对话模式。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多半是以提问者的身份出现, 他的对手才是问题的解释者和回答者,但全部对话的灵魂恰好是提问者而不是回答者,是针对回答的提问才使问题变得更清楚了。然而苏格拉底并不以全知者自居,他说我知道我是没有智慧的,不论大小都没有。与此相反,孔子虽然并不认为自己“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但在对话中,他是以学成者的身份高居于他人之上的。面对学生,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凡是他不知的则是不必知道的。因此,我们不妨称《论语》展现的会话方式为“教化语言”。
观察今天的课堂会话,大都采用“教化语言”的模式,当然其间增加了一些逻辑成分。这种交流并非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交流,而是有很多祈使句或自上而下的表述,依赖一个话语中心和贯穿始终的话题的言谈。教师是主要的讲述者和提问者,教师首先进行知识讲授,然后针对已经讲述的知识进行提问,是以“有知者”身份讲述并发问的。其提问并非是请教学生,而是检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评价学生的学习结果。所以教师一直掌控着问题的答案,并通过实时评价呈现这个掌控进程。教师作为讨论的引领者和课堂的权威,对话过程呈现了知识交流和特定学科“认识”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
课堂作为一个正式的场所,“其中的话语实践有可能受到清晰规则的制约”,因此被辛克莱和库尔萨德选作考察对象。他们把一堂课中的话语实践分解为讲课、相互作用、交流、动议(move) 、行动等五个呈递减序列的单位,发现课堂话语存在一个清晰的结构。他们把这个结构称为“引导性交流”(eliciting exchange) 。它由三个动议组成: 启动(Initiation) 、回应(Response) 和反馈(Feedback),即IRF结构。IRF 结构被普遍认为是课堂正式话语的基本特征,能够描述大约60% 的教与学过程。梅汉(1979) 采用民族志方法,把辛克莱和库尔萨德发现的IRF 结构更加明确为IRE结构,即“教师启动—学生回应—教师评价”。当今的课堂对话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对话。如上所示,制度性对话包含了许多普通对话的实践,但它与日常对话不同。Drew和Heritage(1992)将这些差异的维度系统化,分为以下六点:1、话轮组织——通过教学设计而实现;2、互动的整体结构组织——目标及结果要求;3、顺序——展开的序列;4、话轮转换设计——主题选择;5、词汇或词汇的选择——运用什么语言方式提问;6、认识论和其他形式的不对称——对话中引领话题者与顺应者的不对称。
那么为何今天的课堂话语大多走向制度化的教化语言呢?具体来说,为何世界各国的课堂话语方式没有走向苏格拉底式的产婆术,却走向《论语》式的教化语言?我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一是从心智假设来看,孔子“学而时习之”的形式训练对孩子的学习有立竿见影的成效,由此产生了教师教学的路径依赖;二是从效率角度看,班级授课制是有确定的教学进度的集体教学——这种教学效能的要求需要按单元推进教学,不论班上学生差异如何,都可通过教师的教学控制完成教师设想的教学进度。从学理上说,诘问法能够通过有限的人工步骤(假设、反驳、修正等等)获得正确答案,但步骤太多,过程太漫长,没有谁能到达终点得出结论;三是从规训角度来看,制度性的课堂话语更有利于形成规范要求。
对此作出实践回应的,首推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他的对话式教学包括四个步骤:一是探究;二是解码;三是编码;四是课题外在化。2011年9月,全美教育研究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在匹兹堡主办了一次研讨会,探讨讨论式对话,特别是学术对话在学习中的作用。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对话型教学有能力打破弱势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少数民族儿童和/或母语不流利的儿童经常经历的低要求/低绩效的循环。这种形式的对话增加了认知需求,从而增加了学习机会。学生必须为自己的陈述辩护——例如,引用一篇文章,展示一个数学证明,或者引用科学证据。简言之,学生必须对真理探索过程提出看法。数据表明,经历过这种结构化对话教学的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更好。
综上所述,课堂话语方式包含三个维度:认知性维度、关系性维度和情感性维度。Resnick等倡导的讨论式对话关注的还只是认知性维度。而关系性维度通过对话者的话轮控制呈现不对称的话语权力关系,或平权者之间交流的广度和频率。课堂中的“共识”和“常识”是依托这个维度展开的。在此维度上,文化资本形成是通过对话者与权威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语言价值的影响来实现的。教师可能需要改变话语文化,不仅是改变提问的类型,还要改变学生谈话的价值。在新的语言环境中,知识和理解是共同构建的,教师对学生想法的反应可能是标记什么是有价值的关键。情感性维度并没有直接的认知要求,却涉及着课堂关系中的融洽程度,即有温度的课堂。目前的课堂话语更多还只是一个认知性维度的呈现,仍然着眼于教学的效能问题,更多的课堂探索亟待展开。
/ end /
整理:刁益虎
编辑:胡乐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