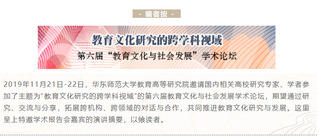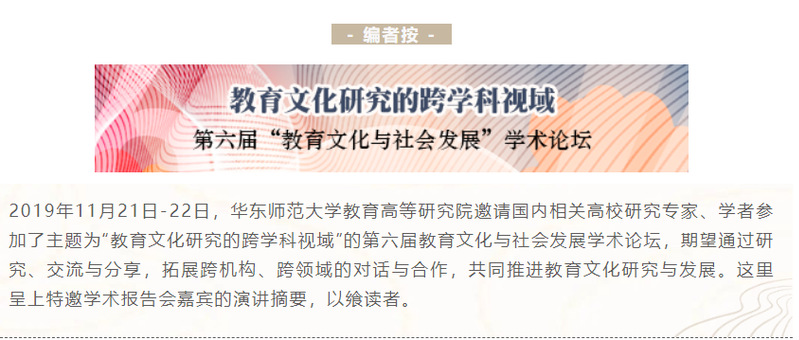
学校文化中的物体系
◆ ◆ ◆ ◆
熊和平 |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按照鲍德里亚关于物体系的符号学立场,学校物件是自成体系的象征符码。物件通过学校采购程序,再经过特定的教育组织形式的编排,从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向了教育的文化价值。师生都生活在物体系所营造的教育符码之中,并形成了学校空间布局的物态语境。人在物体系中穿行。一切静态的学校物件,通过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转化为动态的教育事件,包括上课、开会、做操、文艺表演等。学校场域中的物件及其体系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文化性的,并通过文化价值传达教育意义。
通常来说,“我们的实用物品都参与一到数个结构性元素,但它们也都同时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这是学校物体系具有文化意义的秘密所在。诚然,物件本身并不能构成教育文化事件,但它是教育文化事件的促成者与见证者。学校物件的类型与结构的变迁,意味着教育理念与教育行为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件体系的更新与转型,生成并维系了教育活动史。
根据物件的功用来区分,学校的物体系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建筑类物件,它们对学校校园进行空间的区隔,建构学校空间文化的总体景观,比如教学楼、行政楼、体育馆、校门、围墙等。学校建筑不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实体,是教育活动得以展开的空间基础,而且暗含着特定的建筑理念对学校教育的文化界定。学校建筑不仅安排了教育活动的人际关系与空间秩序,而且表征着主流的社会文化对学校教育的价值要求与活动方式。
以教学楼为例。教学楼是学校物件体系的总体性容器,它不仅容纳所有的教具与学具,还容纳包括教师与学生在内的所有的人。教学楼不仅是一幢庞大的教学建筑,而且是物件体系的总和,是师生关系的总和。教学楼框定了常态的教学手段与方法,它规定了教学体制,甚至教学的方法论。教学活动过于依赖教学楼的空间制度,试图让师生在物件体制与间接经验中认识自然与社会,它是技术性的、符号性的,总之是物性的,与诗性、人性无关。教学楼的玻璃、门窗、砖块等建材体系,来源于现代材料学的基本框架与目录体系。从建筑学意义上说,教学楼受制于工业建筑学的总体规划。教学楼与生产车间在物件摆设、墙壁标语、材料属性,以及空间区隔的行政编码,基本上趋于一致。在钢架结构的力学模式下,教学楼被区分为不同的年级与班级,教师与学生被行政化编码以后,被安置在相应的办公室与教室里。人、物与环境构成了教学活动的三大基本要素。教室的这种结构主义的“人—物”配置方案,致使所有的教学活动都被物体系所规划、所界定,被系统地组合在教学楼图纸预设的“空间氛围”之中。师生处在“物体系”控制整个校园生活的境地,所有的活动都以相同或相似的组合方式维系在一起。在教学楼里,“环境是总体性的,像被整个装上了气温调节装置,安排有序,而且具有文化氛围。”这种对人、物件、制度、行为和人际关系的总体布置,塑造了一种现代性的教育文化景观。
二是教学类的物件,比如讲台、黑板、课桌、实验设备、文体器材等。这些物件在教室的空间关系暗藏了课堂教学的人际关系,并传达了特定的知识论与主体论,甚至形成固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隐喻性的。如果说物是人的影子,那么被规划的学校物件,就是教育事件的影子。物的在场性,就是人的在场性。由此观照,课堂教学改革仅仅停留在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制度文本上还远远不够,改革必将涉及教室空间的改革,只有通过重置教室空间的物件关系,才能为师生双方创造出新的教学家园。
教具与学具的组合方式是一个时代的学校文化与人际关系结构的典型表征。班级授课制组织体系下的秧田式教室的布设表达了教师中心论的教育观念。每个物件按照班级卫生标准摆放有序,其功能性则相互指涉,一起参与到知识秩序与空间秩序的整体结构中。教室通过物件圆满完成了班级中的人际关系的定位,物的行政化表征了人的行政化,以及知识传授的制度化。作为教学组织形式的重要物证的课桌椅,其前身是教具工厂的产品,它们之所以有销路,不是因为比较便宜,而是因为它们身上附载了官方的教育信念及校长们的默许。教具在进入教学楼与教室之前,通常是作为待售的商品堆放在仓库里,它们还没有获得教育学的属性,也没有教育文化学的特征。教育文化通常以一个群体长期积累的习俗性观念为基础,并抽象在一些符号性的物件体系之中。物件是关系性的、空间性的,它们被组合成一定的顺序、方位与临界点,最终形成特定的物态关系及其教育气氛。
三是制度类的物件,包括课程表、作息表、考勤表、学生守则、班规、流动红旗、检讨书、荣誉证书或奖章等。教学制度通常需要以文本(或特殊材质)的方式汇编并保存下来,这就构成了学校制度文化的物质基础,它是教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表格、制度文本与荣誉符号等承载了“教学的文化史”,它们会“说话”,并有自身的一套话语规则,引导教师与学生的教学进程,使他们养成一种基于特定制度环境下的“规训与惩罚”的教学习俗。
相对而言,制度性物件的直接功用性较弱,它们不是拿来用的,而是拿来监督人的,并直接作用于人的观念与思想。它们相互依存,一张表格指向另一张表格,一种惩罚性制度对应另一种奖励性物件。正如纸张并非简单的制度文本,它承载了教育观念与文化价值,它不是制度本身但它规定了制度。如果说,黑板、刷子、扫把、抹布、课桌椅、电子笔等日常用具构成了学校物体系的底层结构,规制了“人—物”互动的经验方式,那么,制度性物件则形成了物件关系与使用方式的顶层设计,奠基了学校物件类型与组合方式的物态形而上学。学校物体系依赖于制度性物件的稳定的配置结构,它们是学校物件文化的DNA,具有遗传、繁殖与再生产能力。单个的物件并非是自足的物,任何物件都依赖于物的体系,一个物件必然指向另一物件,并在物件的相互指涉中传递共同价值。因此,物件之间具有一种价值共谋关系,犹如信息流的传递过程,“每一个信息首先指向另一个信息,而不是指向真实世界。就好像一个媒体总是指向另一个媒体,它们在演变中好像具有一种内在的目的性。”也就是说,表格、规章以及奖惩性物件,都是信息流中的不同环节,它们聚合在一起并非指向真实的教育世界,而是指向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教育符号世界。
四是日常生活类的物件,比如学生的书包、文具、校服、红领巾等,教师的教学资料包、电子教具、着装配饰等。这类琐碎的日常用品同样拥有“场域性”与“教育性”,它们不仅被使用,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被赋予文化价值。考察师生的学校生活物件的文化属性,实质上就是考察这些物件从工具性到教育性的文化传递过程。在教育文化研究的视野中,生活物件也蕴涵了文化认知与接受的过程。物件既作为工具,同时又作为文化符号存在于学校教育的现场。
学校场域内的生活类物件的社会生命与文化属性,不同于其他消费空间领域的物件。它们的商品属性被弱化,教育文化属性得到了擢升,具有诗学与艺术等人文因素。比如书包、橡皮、文具等进入诗歌、校园民谣等文化领域,教师的粉笔、讲稿、日记等进入电影、文学等艺术领域。师生生活类的物件,“是真正的物,是现象中的物,是主体感知的内容和活生生的经验——介于现象学的实体与伯格森主义的实体之间的存在,它与形式对立。”生活类物件虽然有它的商品形式,但在这种形式背后,有深厚的教育文化印记。生活类的物件往往具有纪念意义,它们承载了教育生活史的记忆,是教育博物馆的收藏对象。从经验的物到象征的物,物件在使用过程中被人格化了,人也在物件文化的场域中被物态化了。尽管在教育消费时代,生活类物件的使用周期在不断缩短,但是它的教育用途以及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浓缩了学校物件与教育事件关系上的复杂性。
总之,学校的物件体系不仅有工具意义与技术价值,而且还有文化意义与教化价值。重视学校物件的教育文化研究价值,需要从文化研究的学科史的高度来反思人与物的关系及其转型的方法论基础,以便了解当代教育的物件文化的处境。物会教育人。在人与物之间存在知识与道德的发生学机制。学校物件的文化研究,是立足于校园的教育实践研究,从中可以开辟一条以物体系为切入点的人文性的教育研究路向。这对于揭示当前我国学校物件文化的总体面貌、基本特征,以及推动学校文化的建设与创新,都有益处。
/ end /
编辑:胡乐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