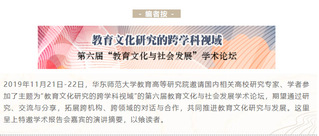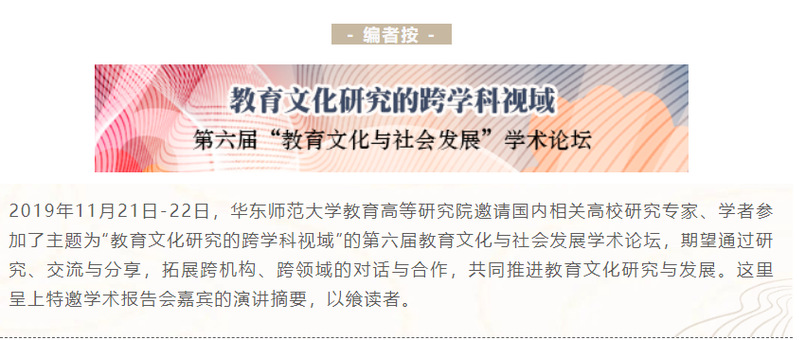
家校关系:结构化转型与互动逻辑
◆ ◆ ◆ ◆
唐晓菁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讲师

近些年,家校关系的种种现象备受关注。在教育改革的视野下,已有的讨论大多围绕着“家校合作”的政策与实践意义展开,其中亦不乏对国际经验的引介。不过,现实中的家校关系显然更为复杂。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家庭与学校之间边界变得模糊(Porcher,1981)。学校影响或者“侵入”家庭生活,而家庭也透过各种方式介入学校教育(Georges Fotinos,2014)。在中国的语境下,家校关系的问题更为突出。一方面,学校对家庭的“裹挟”、“僭越”,将之变为学校附庸的现象不时被媒体与学界所曝光、批评(刘利民,2017;王丽美,2018;贺春兰,2019)。另一方面,在如今的家校关系中,教师作为“师者”的权威形象远不如从前。教师被家长挑战、诟病,甚至施以暴力的现象亦时常见诸报端。那么,如何理解家校之间充满悖论的关系?笔者认为,仅从狭义政策分析角度不足以阐明经验层面上家校之间的关系实质。事实上,家庭与学校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受个别、短期教育政策所调节,而且与学校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以及在社会系统中家长与学校教育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将家校关系纳入结构视野之中,以理解两者之间互动的动力机制。
/一/
家校关系的结构性转型
自上世纪末以来,教育市场化成为全世界教育改革的普遍趋势。关于这一场变革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效应已有较多的论述。但较少被讨论的是,教育市场化也意味着国家与学校之间关系的重构,从而带来学校功能转型与教师职业重构的后果。将视线稍为拉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学校的诞生也是由国家“接管”教育的过程——家庭从此转向“私性化”领域,从经济、教育等功能中解脱出来,仅承担初级社会化的情感支持、伦理教化等职能。而学校则需要承担知识技能教学、现代公民素养的培养以及人才的筛选、分流等工作,以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与工业化体系的需要。自此,学校实际上主要承担着“传道”——社会化与文化传递与“授业”——知识技能的传授与筛选分流,这双重社会功能。前者意味着文化上的传递与社会整合,而后者指向社会分化。长期以来,这两方面的功能处于大致并重与重叠的位置。正如布迪厄等学者(P.布尔迪约,帕斯隆,1985/2002)所揭示,即便在教育民主化之后,由于知识和技能中渗透着优势阶层的统治性文化,因此学校在维持其文化合法性的同时,也完成了阶级“再生产”。换言之,学校文化整合的功能与分化功能同时实现。这一功能重叠导致阶级地位隐蔽的代际传递。但有必要注意的是,无论如何,当时学校既作为公共机构,又作为文化上具有合法性的单位,这使得教育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这一情况随着教育市场化变革的推进而改变。改革使得学校之间竞争的逻辑逐渐超越了教育共同体的逻辑。也就是学校的教育文化整合的功能更多让位于以分流/筛选为目的的知识技能比拼的竞争目的。法国学者赞滕(Agnès Henriot-Van Zanten,1996)敏锐地指出法国公立学校中的这一变化趋势。她认为,教育自由化政策导致公办中学“去中心化”,各个学校被要求拥有自身的特色与自主性。以此名义下,学校逐渐从过去服务于公共目标的文化权威机构,转变为必须为了争取资源而相互竞争的市场化机构。吸引“好学生”、维护学校的良好社会形象,进而获得财政支持,这成为学校最为重要的工作。由于这一功利化的工作目的,教师的职业性质也随之改变。他们必须强化其教学职能,而弱化“育人”的工作。这既引发了教师的职业道德危机感、又改变了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关系。根据赞滕的如上分析,不难看出,学校功能的转变,即从过去传道授业的“育人”机构转向业绩主义、功利主义的,以筛选、分流为功能的组织,对家校关系转型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透过“家校合作”的具体实践,由于教师与家长之间互动变得更为密切,学校的功利主义带动了家长的竞争意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学校“培养人”的目标不再明确,其文化上的统合性减弱,继而引发了家长在文化与身份认同方面的焦虑。正如一些“择校”研究所呈现,学业竞争仅仅构成择校的部分理由,文化与身份认同方面的建构也是家长教育行动的重要动因。不少中产家长通过择校旨在帮助子女进入特定的社会化环境,如选择生源趋向于同质化的学校,以减缓其在子女社会化与人格培养方面的教育焦虑。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社会各阶级家长与学校之间关系也发生转型,教育的流动性功能更受重视。如上所述,在西方语境下,虽然教育民主化影响了学校的生源分布,但由于阶级文化的分裂,中产阶级的文化“惯习”与教养方式有利于其子代在学校中获得成功,而工人阶级并不重视教育流动,存在“自我放弃”的一面(保罗·威利斯,1977)。因此,在上世纪中后期之前,中产家长主要依赖于学校实现阶级的再生产,不需要投入过多的额外经历。上世纪末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就业环境以及福利体制等方面的变化,社会各阶级与学校的关系都发生了转变。首先,不少研究发现,工人阶级家庭越来越重视学校的社会流动价值。在劳工阶级整体社会地位下降、失业率上升、工作条件与保障削减的背景下,前者日趋将子代的未来寄托于学校带来的阶级跃升机会。其次,对中产阶级而言,劳工阶级与学校阶级的转变加强了他们代际地位再生产的不确定性。更多家长意识到必须付出努力,而非仅凭“惯习”,以避免被工人阶级的孩子追上。事实上,中产阶级家长的焦虑感尤为突出。一方面,相比于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因而可以自由选择昂贵的私立学校从而实现“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韦伯,1921/2010)的上层阶级,中产家长必须更多依靠公立学校,需要更为策略性地应对教育竞争的挑战;另一方面,近些年来,中产阶级内部的教育竞争也不断上升。二十世纪末的经济危机带来学历回报延迟、就业市场中竞争压力加剧,这些结构性原因对世界各国的中产均构成压力。在西方社会的失业危机下,部分中产还面对职业的不确定性与失业风险。这些经济与职业机会方面的变化对中产家长构成挤压,强化了后者延长子女受教育年限、高度策略性建构子女的教育路线以期在教育回报不确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占取优势位置的心态。
/二/
被工具化的学校与“共谋”关系
理解上述两方面的结构性转型,才能更好分析“家校合作”这一政策落地之后的家校互动关系。首先,无论是从学校变革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各阶级家长身处的阶层流动压力角度来看,学校都处于逐渐被工具化的境地。换言之,教育的流动性功能挤压、侵占了其他的功能。而在这一点上,在竞争压力越大、福利越弱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各阶级对教育的流动性功能需求也更为强烈。那么,家长以各种形式卷入教育的动力也就愈加突出。其次,学业竞争的加速并非来自于家长的“功利主义”,也不由具体学校或者教师所决定,而是出于学校、教师与家长之间的结构性“共谋”。而“家校合作”作为教育自由化的一项具体政策,进一步强化、扩大了家校之间互构或共谋的空间。在这里,有必要突出教师职业共同体与职业自主性的重要性。如上文所述,在家校关系的复杂转型过程中,教师夹于学校功能转型与家长诉求变迁之间的中间位置,其职业伦理受到极大挑战。而教师共同体有助于缓和教师个体的职业困境,“抵御”来自国家、学校与家长的多方压力。同时,“共谋”的视角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即便在“教育减负”的背景下,学校仍然能够“裹挟”家庭,将之转变为“第二课堂”;以及为何在教育如此受重视的社会中,教师职业权威却日渐式微的问题。事实上,正是由于“共谋”的背后是功利性的流动目的,而非对教育本身的尊重。因此,教师在偏重于强化其提高学生成绩的技术能力,而弱化“育人”角色的同时,既无可避免地遭到来自于社会的诟病,又反而削弱了其职业的正当性。
/三/
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挑战
家校关系结构性转型的分析视角不仅有助于理解家校之间的互动逻辑,而且对教育社会学研究提出了重要挑战。首先,从学校研究角度来看,教育社会学长期以来以学校教育为研究中心,研究者大多试图理解学校内部的教育“黑箱”问题。家庭更多被认为经由阶级文化对学校中的教育产生影响。那么,在家校关系已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则需要更多理解家长的教育介入行动如何参与建构教师的职业,以及影响学校内教育过程的问题。其次,从家庭教育研究角度来看,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受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关于文化资本与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这些研究聚焦家庭内部的教育过程,但很少讨论家长如何积极行动以应对学校变革以及自身阶级处境所带来的种种焦虑。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化资本、惯习以及教养方式等结构化研究路径有必要更新为行动研究、策略研究等范式,以更好理解在新的教育场域空间中的家庭教育参与。最后,家校关系的结构性转型实际上带来教育流动体制的复杂转型。一方面,文化资本或者经济资本的“再生产”范式虽然有助于理解阶级之间的分流问题,但很难说明阶级内部的竞争与学业流动机制。另一方面,家校关系的转型导致了诸如教育竞争不断提前、“减负”失效等多种教育改革未预期的后果。因此,如何理解家校“共谋”关系下学校分流体制的形成及其对教育的影响,也构成了教育社会学研究有待探索的重要议题。
/ 参考文献 /
1. P.布尔迪约,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商务印书馆,1985/2002.
2. 保罗·威利斯.秘舒,凌旻华译.2013.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M].译林出版社.
3. 贺春兰. 家校关系:舆论诉求与回应建议——从舆论视野看我国家校关系的演进和趋势[J].教育科学研究.2019(07).
4. 刘利民.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边界[J].中国教育学刊.2017(07).
5.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21/2010.
6. 王丽美.“家校群变成‘负担群’扭曲家校关系”.《河北日报》.2018/8/30.
7. Georges Fotinos,2014. L’Etat des relations école-parents : entre méfiance, défiance et bienveillance. Une enquête quantitative auprès des directeurs d’école maternelle et élémentaire.
8. Porcher,L. 1981. L’école des famillies. In MARIET, F (Ed.), L’enfant, la famille et l’école, Paris : ESF.
9. Zanten, Agnès van. 1996. Stragétie utilitaristes et stratégies identitaires des parents vis-à-vis de l’école : une relecture critique des analyses sociologiques. Lien social et Politiques No.35. pp 125-135.
/ end /
编辑:胡乐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