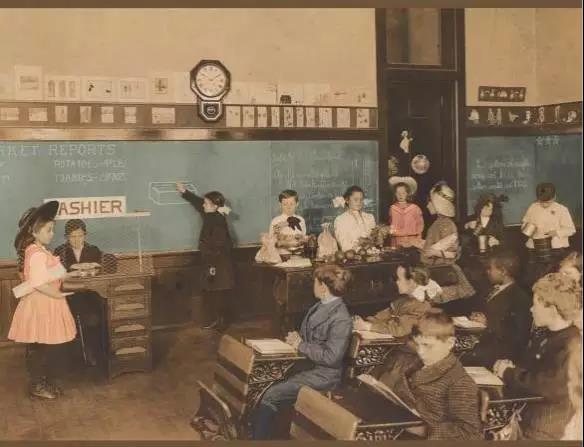
王文智. 美国课程史研究的演进[J]. 教育学报, 2016,1.
摘要:课程史研究在美国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后,不断从史学和课程理论中汲取养分,发展为一种独特的课程探究方式,并实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还原到解构、从中心到边缘”的研究重心转移。结合课程理论和史学研究的整体学术境脉,可从三个维度考察美国课程史研究的演变趋势: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再转向新文化史;从重构史学到建构史学再到解构史学;关注的“主体”从单一转向多元,再转而对作为历史的建构物的“主体”本身进行反思。
关键词:课程史;课程理论;美国教育史;后概念重建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Curriculum Histories
WANG Wen-zhi
(Institute for AdvancedStudies in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After its independence asa research field, curriculum history kept absorbing theories from history andcurriculum studies, became a unique form of curriculum inquiry, and made the shift of its focus from macro level to micro level, fromreconstruction to deconstruction, and from the center to the edge. Takenthe context of both curriculum theories and historical studies intoconsideration, the evolution of curriculum historical studies in America wasdescribed in three dimensions: from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social history, thento cultural history; from reconstructive history to constructive history andthen to deconstructive history, from a single subject to multi-subjects, andthen to rethinking of the “subject” as a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Key Words: Curriculum History, CurriculumTheory,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Post-reconceptualization
2010年以来,美国课程史研究在我国逐渐受到教育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的课程研究多年来因较多地借鉴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课程理论而被人批评为“简单移植”、“食洋不化”。批评者认为当前课程改革的理论源头和实践园地相去甚远,不顾理论诞生的具体社会文化情境而草率地借鉴使用,远水难解近渴,甚至会出现“水土不服”。美国课程史可以帮我们了解孕育出这些课程理论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态,从而认清在理论迁移到新的环境时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其效用的发挥。二是了解美国课程史学,可以为本国开展课程史研究提供借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之后,已经进入反思和调适阶段。如何理解和评价发生在特定历史时空内课程活动的意义,如何整理和利用历次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如何发掘和继承我国既有的课程思想资源和制度遗产,如何考察和认识我国现代课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得失,要回答这些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就要先来思考“如何开展课程史研究”。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课程史研究,美国课程史学历经四十余年发展已经有了比较厚重的学术积累,回顾和分析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能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发展概况
我国课程学界对西方课程史研究成果的借鉴,已经从对经典范例的个别介绍[1],转向对不同典范的综合比较[2],并开始对研究演变历程作整体上的把握。受台湾课程史学者的影响,大陆研究者目前也将“萌芽期”、“奠基期”和“修正主义取向”[3]等词汇作为描述西方课程史研究的阶段性标识。例如,有研究者将美国课程史研究分为三种取向,即,“进步取向”、“修正主义取向”和“文化历史取向”[4]。不过,当前对美国课程史研究“取向”的认识当中也有不少误读。比如,“进步”、“修正主义”和“文化史”是属于不同范畴、不同层级的概念,将它们作为三类课程史研究的标识,进行并置和对比,并不恰当。一些属于一般教育史研究的著作被国内学者当作了课程史某种取向的代表作①;而包括学校科目的社会史在内的“课程社会史研究”本是美国课程史领域中“作品最为丰富的一支”[5],却因归不到任何“取向”中而被忽视了。
为了把握美国课程史的整体演变趋势,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已具备独立研究意识的专业化的课程史研究,而不是其他学术作品中涉及课程史的章节段落甚至只言片语。正如富兰克林(Franklin,B.M.)所强调的,应该将课程史作品与“为课程史研究提供史料的早期课程文献”区分开来,课程史研究的核心不是“那些对课程问题偶感兴趣的教育史家”的著作,而是具备丰富的课程理论知识和深厚的专业情感的课程学者的学术努力。[6]依据这样的标准,课程史研究的真正勃兴应当不早于20世纪60、70年代,因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其标志不是某一孤立的文本的发表,而是学术共同体形成了某种共同的旨趣。在这一时段,包括重要著作的问世和专业学会的建立等一系列事件,表明课程领域内外种种条件的具备和课程学者自身历史研究意识的觉醒,课程史研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成为独立研究领域之后的数十年中,课程史研究先后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参照北美课程研究领域出现“范式转换”的情况,可以将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前概念重建”、“概念重建”和“后概念重建”三个时期。
(一)前概念重建期
美国课程史研究成为课程研究当中一个独立的分支领域,与概念重建运动之前课程学界遭遇的专业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课程史研究的最初动力是整理和反思课程领域的学术遗产,人们借此思考课程领域“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危机。早期的课程史学围绕着课程学术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希望通过回顾课程领域发展的历史,帮助课程工作者重拾专业信念。课程史研究协会的建立者坦纳夫妇(Tanner, D& Tanner ,L),从教育工作者的立场出发描绘了美国课程思想的进步历程[7],尝试整理课程领域中已有的成果,以便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8]延续对课程核心问题的思考,推动课程领域继续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而克利巴德(Kliebard, H.)等人则揭示了美国课程思想的多样性,通过刻画不同学术团体间的思想冲突来解释课程演变的历程,并在历史的情境中认识早期课程研究的局限性,借此寻找突破和超越的可能。克利巴德的课程史研究为课程领域的“概念重建”提供了重要基础,他和坦纳夫妇是“前概念重建时期”课程史研究的代表人物。
(二)概念重建期
而“概念重建运动”兴起之后,课程研究者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此时批判性课程研究已极具声势,这些研究指出课程不是既定的也不是天然的,它有自己的历史,现实中的种种不公都可以在历史中寻得源头。要支撑这样的观点,就需要把“课程知识”获取现有地位的历史过程发掘和展示出来。既然将课程看作一个社会冲突的竞技场,那就应该借助历史研究对不同集团在其中的行为模式描画清楚。例如,富兰克林等人通过历史个案研究描绘了地方层面具体的课程运作,并分析了意识形态对课程实践的作用机制;还有一些受英国课程史学家古德森(Goodson, I.)影响的美国学者开展了科目史研究,描述学校科目在特定时空场域中的历史形成,揭示学界、工商业和政界的不同社会力量如何相互斗争以求将代表自身利益的知识合法化。学校科目史和课程历史案例研究在美国兴起,顺应了概念重建运动深化课程研究的需要。
(三)后概念重建期
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当“概念重建运动”已然远去,新一代课程学者开始使用“后概念重建”的概念探讨课程领域的当前状况和未来走向[9],课程研究的各分支领域相互交融,以及种种“后”理论的全面渗入是后概念重建期课程研究的主要特点。因此在这一时期,课程史与课程研究的其他分支领域(如女性主义课程论等)相交叉而产生的成果尤为引人注目,它们构成了课程史研究的新取向。比如亨德里(Hendry, P.)等人就发掘了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课程历史,揭示这些边缘人群是如何成为“他者”而被排斥的,同时借助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考了课程史研究该如何处理性别和种族等关于“差异”的主题。波普科维茨(Popkewitz, T.)学派则依循福柯式的历史研究路径,反思当前课程理论和实践中使用的话语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并揭示了其背后的权力意蕴。研究者在继承了之前的课程史学的政治关切和批判取向的同时,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认识到语言本身对历史书写的限制作用,开始对课程史学的叙述方式进行深入反思。
二、美国课程史研究演变的三个维度
上述阶段划分主要考虑了课程研究的典范转移对课程史学的影响,作为课程论和教育史学科交叉所形成的研究领域,课程史研究的演变同时受到两个“上位学科”学术发展的影响。如果将课程史领域独立之后的数十年间教育史学乃至历史学的整体学术演变也作为参照,可以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重构历史—建构历史—解构历史”和“单一主体—多样主体—反思主体”三个维度把握美国课程史研究的演变。在这三个维度中,其一我们要考察课程史研究如何看待“课程”,其二要考察它如何看待“历史”和历史研究,其三要考察它如何看待课程和历史当中的“主体”。
(一)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
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之间的转换这一维度理解美国课程史研究的演变时,我们不仅希望考察研究内容的重心转移,同时也关注研究方法的更新。不同时期的课程史研究在讨论“课程”时,所说的是学术思想还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活动,又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与研究内容的转换相伴的,是“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等史学潮流在研究方式和方法上给课程史研究带来的冲击。
贝拉克1969年对当时美国课程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概述[10]],他总结的课程史研究的四个主题中有三个都属于课程思想史。思想史的一度兴盛与课程作为一个智力/思想领域受到的严重挑战不无关系,正是由于课程开发研究范式遭遇了危机,课程领域对教育实践的影响日渐微弱,研究者们才开始反思这一领域原本“非理论”和“非历史”的倾向。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希望通过回顾本领域的往日荣光,鼓舞士气,让课程工作者在困局中保持对专业精神的坚守。除了专门回顾课程领域重要学术思想的论文或专著,课程专业教科书当中对课程思想演变历程进行梳理的章节,也是早期课程史研究的重要形态。坦纳夫妇通过历史研究指出外在政治力量的干预是课程改革出现“钟摆”现象的原因。他们认为,课程工作者不应盲目跟从外部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抛弃本领域的核心思考,而要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推动领域朝专业化的方向继续发展。而另一些课程研究则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早期课程研究的局限性,借此寻找突破和超越的可能。例如克利巴德的课程思想史研究对哈里斯、霍尔、博比特、查特斯和泰勒等人的课程思想的局限性做了深刻的批判[11][12]],并成为推动概念重建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
然而当课程领域进行了概念重建之后,单纯的思想史研究就无法满足理论建设的新需求了。当广泛借鉴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新一代课程研究,与倡导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联姻的新社会史“产生共振”,课程社会史的崛起便不可阻挡。课程社会史研究不满足于仅仅考察文件、报告、著作和论文中反映的主观认识,还希望了解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学校里究竟教了什么,又为什么在教这些。研究者一方面通过地方和学校层面的案例研究打开了学校的黑箱,将历史研究的目光从“课程辞令”转向“课程实践”;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史研究揭示特定的知识如何在各种社会势力的激烈斗争中取得合法地位。英国学者古德森的科目社会史研究[13]为美国课程史学者树立了典范,而富兰克林的《构建美国共同体:学校课程与对社会控制的追求》一书[14]则反映了原本偏重思想史研究的课程史学者群体也开始积极地通过案例研究来打开新局面。除案例研究外,统计方法的使用也显示出当时课程史研究与“新社会史”的亲和。关注重心和研究方法的双重转变体现了课程思想史与课程社会史之间的差异。
课程思想史和课程社会史也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在这些研究中,结构和事件都被置于一个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序列里,一个接一个,相互牵连,相继出现……关于学校的历史叙事都表达着民主的进步希望,以及与社会控制和结构性不公等问题的抗争。”[15]思想史研究注重精英的理性力量,相信“伟大的理想包含着自我实现的种子”[16]。课程社会史研究较之思想史有更强的批判性,关注到课程的“社会控制”属性,将课程的社会性和政治性面相展现给读者,然而却也仍未摆脱“行动者与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此社会史要么同思想史研究一样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抽象的“主体”身上,要么悲观地认为“行动的原因与社会主体的能动性毫无关系”[17],主体性只是对人类置身其间的社会背景的某种反应或表现。
而后概念重建时期出现的带有新文化史色彩的课程史研究首先颠覆了以往历史书写的惯常假定,突破行动者与结构的二元对立,将“主体”和“进步”去中心化。[18]这些研究借助后现代理论,以课程话语作为中心展开研究。这并非是思想史研究的简单复归,话语不是只居于精神世界的抽象存在,而是同时具有某种“物质性”。这些话语“构造了课程实践的场域,同时课程实践又反过来加强或者修正了它们”。即便同样是处理权力和社会控制等主题,受新文化史影响的课程研究也展现出与社会史和历史社会学研究截然不同的风貌。[19]10课程社会史认为学校知识执行着社会控制的监管和压制性功能,知识被看作是某种反映着社会利益和社会力量的“东西”,没有把它本身看成是权力建构中的生产性实践——而这正是文化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从把知识当作社会控制的附带现象,转向把知识当作一个文化实践和文化再生产的领域,这是课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转变。
文化史一方面用“身份、意识和心态等替代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力的经济基础”[20],使用文化人类学的方式丰富和修正了社会史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同时又“打破了传统思想史惟精英人物、知识阶层的狭隘偏见,用一种更广义的文化概念,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20]有人用“文化之战”来描述文化史的兴起给课程史乃至教育史领域带来的巨大冲击:这场变革裹挟着审美的、伦理的、阶级的和性别的价值关切,将“文化”作为审视和把握所谓的“晚期现代性”或者“后现代”的种种难题之关键工具。这种后现代历史探究,并非是“反现代”的,也并未遗忘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观念,而是一种现代性(如解放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后现代性(如拒斥宏大叙事、关注语言的作用)的复杂而精致的组合[19]8-9。
(二)重构历史—建构历史—解构历史
在考察不同时期的课程史研究在理解“历史”和处理“历史研究”方面的差别时,本文主要参考英国后现代史学家蒙斯洛(Munslow, A.)对史学类型的划分。蒙斯洛用重构历史、建构历史和解构历史(History as re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deconstruction)的概念区分了历史学者们开展研究的三种不同方式[21]20。蒙斯洛认为身处“后现代状态”中的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对历史书写的既存认识,不把一些历史哲学问题思考清楚就无法应对新时代对历史研究提出的挑战。因此他从一连串基本问题②出发,来考察人们在思考和撰写历史的时候彼此间有着怎样的差别。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解答,显示了史家们对历史研究的不同理解。
在历史研究中,重构主义者相信历史研究生产的是客观可信的知识,历史学家可以通过特定的方法在过往事件留下的踪迹中获得关于过去的准确认识。重构主义者通常认为历史是一个独立的基于经验的学科,是对事实的客观重建。历史研究就是要根据原始资料、依赖原始资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他们继承了兰克史学的传统,强调“如实直书”,以理性的、独立的和全面的调查为基础,避免意识形态的干扰[21]20,史学家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应该淡化,更不要过多地去借助理论。重构主义者认为历史与社会科学有着巨大差异,他们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反理论”的倾向,反感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对历史领域的侵染。[22]
与之相对的,建构史学则积极地使用社会科学理论来处理历史,一些人甚至认为历史研究必须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中去。[21]24建构史学认为特定的事件都是某种可辨识的行为模式的组成部分,而这些行为模式则反映了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历史研究不仅仅要处理史料,而且要将实证证据置入一定的理论框架内(这些理论源自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探讨的通常是人类活动的一般规律),这样历史才能得到解释。与重构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是,建构史学在运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解读历史时往往带着强烈的批判意识,通过书写历史为边缘群体声张正义,从不回避意识形态的问题。尽管有上述这些差异,建构史学与重构史学同样都以客观性作为前提,都默认语言在描述世界时不会有任何障碍,语言建构的意象与世上的事物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而“随着解构主义的兴起,历史将不再是对过去真实探寻的建构,历史或可成为历史学家在当下语言的、叙述的创造物。”[22]解构史学认识到历史学家的主要作用是叙述一个故事,而叙事的基础来自他们对其他叙事的理解。这种叙事的基础总是先于历史经验,重构史学将自己的先设隐藏了起来,建构史学将这种先在的解读用社会科学理论表述出来,但他们都坚信自己历史书写完完全全是基于史料而不是基于先设。然而在解构史学看来,历史学家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这些先设,它们会在叙事的过程中,在给过去赋予情节,给故事设计结构的时候展现出来。对解构主义者来说,历史可以看作是文学的一种形式。解构史学对待自身的叙述和解释抱着深入反思的态度,要求研究者意识到自己进行历史书写时使用了语言,而语言并非是透明的,它本身对书写活动有所限定。历史写作对过去进行了怎样的“处理”,叙述语言又为之凭添了什么色彩,这些问题都不容回避。
前概念重建期的课程史研究,大多属于重构史学,或者介于重构和建构史学之间。例如坦纳夫妇认为“严肃的历史均是重构物”[23]3,需要以学术的客观性去探究历史,他们反对修正主义史学家从理论命题出发,在历史材料中寻找证据支撑自己的命题,因为这样会“将类型和形式强加于材料之上”[23]26。克利巴德的《美国课程斗争:1893-1958》(下文简称《斗争》)则更清楚地体现了一种从重构史学到建构史学的转变。《斗争》的第一版同诸多重构主义历史作品一样,没有明确地说明作者在使用什么样的理论解释史实,把自己的理论预设隐藏于叙述中,所有的论点都“内蕴于显在的故事里”[24]131。而数年后《斗争》再版时,克利巴德决定吐露自己的心迹,将藏在背后引领着自己的叙述的理论框架点明,他在第二版的末尾加上了一篇后记并在其中指出,理论方面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指引着这部课程史的撰写工作,只是起初他自己对地位政治学等相关理论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所以才没有明说。[25]
概念重建时期的美国课程史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紧密结合,社会阶层、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理论概念成为观察和书写历史的有力工具,研究者不再局限于使用基本的叙事逻辑来组织材料,还凭借抽象的理论思维获得关于人类行为规律的一般认识。很多时候可以说,如果不是借助了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者不可能如此深刻地认识课程历史,揭示埋藏于表象之下的深层机理。学校科目的社会史研究尤为充分地体现了建构史学注重利用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这些历史研究以修正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出发点和旨归,史实成为理论建构所需的实证材料。在建构主义的课程历史研究中,与其说研究者的分析源自事实,不如说事实来源于分析。没有理论工具就发掘不出真相。在行文方面,研究者倾向于在呈现结果之前先介绍分析的过程,在展开分析之前先明确地表述自己用以构架思维和论述的理论框架。
而“后概念重建时期”的课程史,则展现了解构史学的研究特点。波普科维茨、贝克(Baker, B.M.)和亨德里等研究者都不赞同历史研究的任务是探究外在于人的“绝对事实”,而将话语置于历史考察的中心位置。课程领域中最常用的概念,“课程”、“儿童”和“教师”等,本身都是话语,是历史的建构物,而并非某种现实的简单对应物。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叙事的关键作用也被凸显出来。历史并非仅仅由所谓的证据和事实构成,历史解释是一种语言行为,是一种文学创造。正如亨德里指出的,“以往的课程史研究希望人们将叙述的产物当作现实”[26],而解构主义的历史研究帮人们看清那些所谓的现实乃是话语建构。“过去本身并没有故事、叙述、情节设置或论证,过去也不存在任何节奏或理性;过去本身并不内在地具有历史的身份,过去是通过历史学家的工作转变为历史的”[22]。以往的历史学家不加质疑就假定在语言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相互分离同时又相互对应的关系,解构史学家则朝着“去指涉化”的方向努力,抛弃了这种假设。他们认为语词的意义是任意的,是后天被给定的,本身负载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而并非是价值无涉的。
(三)单一主体—多样主体—反思主体
对历史中的主体问题的不同处理,是理解课程史研究发生变化的又一重要维度。这里要谈的“主体”并非历史认识的主体(前面两个维度已经就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探讨),而是历史故事当中的“人物”。与小说不同,历史叙事并不能随意虚构一个具体人物,而只能在历史材料中选取人物纳入到自己的叙述中来。但叙事中选取哪些人物又忽略哪些,则属于历史学家的自由。不仅如此,当借助理论认识进行抽象以后,历史学家还可以处理虚构的“人的类别”,例如人民、统治者和“优势群体”等,并且可以把这些主体类别当作是超越时空的绝对化存在。由此史学家可以对人做一般化的处理,遮蔽其具体意义。
在美国历史研究中,高举“进步主义”的大旗,使用综合性原则将美国经验捆绑在一起,构造属于所有美国人的共同的“伟大故事”,便是一种在历史叙事中塑造单一的、抽象的主体的典型努力。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Beard)的著作所表现的那样,进步性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最高、最典型的表达”[24]69,整个故事是某种单一群体的意志的实现过程。坦纳夫妇的《学校课程史》就尝试在课程领域构造比尔德式的伟大故事,用“进步主义教育”的概念将他们笔下的课程事件全部统摄起来。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只是对某些教育家的课程观点进行评述,然而作者们却相信这些精英的言说能够代表美国课程思想与实践的“主流”。
然而,对于进步主义教育究竟是什么,美国学界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进步主义的课程思想”的内涵也是人言人殊。克列巴德从根本上质疑所谓“进步主义教育”的存在,他的《美国课程斗争:1893-1958》通过刻画人文学科论者、儿童发展论者、社会效率论者和社会改良论者这四大“利益群体”之间围绕美国课程展开的斗争,将一种传统化为多种传统,将一个声音化为多种声音。《斗争》摆脱了目的论的干扰,历史不再是宏大目标的必然体现,而是包含了多种可能,历史的走向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克利巴德考察的对象仍然是精英群体,但却向课程历史主体多样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无论坦纳夫妇还是克利巴德,“前概念重建期”的课程史研究关注的人物都限于著名学者和身居高位的教育管理者,关注重心出现转变则有赖于人文社会学科研究风气的转移。上世纪60年代末激进的社会氛围或早或晚地影响到了美国学术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历史研究中的“新左史学”、“新社会史”,还是教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教育史学、批判的和政治学取向的课程研究,都将关注的焦点从精英转向下层。于是在“概念重建期”的课程史文本中,我们逐渐看到了各种社会力量的身影,普通教师、家长、学校管理者乃至工商界人士都被纳入到课程故事中来。不仅如此,课程历史也不再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的历史,少数族裔和女性的课程经历也被发掘出来,用以修复历史的残缺,课程史所描述的“主体”前所未有地丰富了起来。课程领域在经历概念重建后将研究关注的重心从中心转向边缘,课程史研究也同样如此。然而边缘群体打破缄默后,却又面临着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即为什么张开了自己的嘴,却或多或少地在说着别人的话?
仅仅将先前被排斥在外的群体填补到新的历史叙述里,把边缘人群受压迫、做贡献乃至求解放的经历书写出来,虽然对主流历史构成了有力的挑战,但却并不能化解区隔、对立和偏见,甚至将这种差异本质化了。明明是历史研究,却将女性、黑人等主体概念作为非历史的东西使用。
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之后,学者们开始对研究使用的语言进行反思,中产阶级、工人阶级、黑人和白人等原本在历史书写中被不加质疑地使用的“主体”范畴,成了历史研究首先要质疑和考察的对象。人的类别并非是“给定的”,而是历史的构造物,无论是“黑人”还是“女人”都不具备某种永恒不变的本质,“各种‘本质’范畴的内涵无非是人对各种对象的关键内容的想象性构造和推理性猜测”[27]。“如果说概念重建时期的课程史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对知识的非中立性的认识使得知识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受到重视,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和反种族主义的理论受到欢迎;那么1990年代以后‘后概念重建时期’的课程史研究则对概念重建阵营的本质主义倾向进行了质疑,新近的欧陆哲学理论开始产生影响。”[28]先前研究的努力方向是将历史叙事中主要行动者(the main actors)的外延扩大,将原本被排斥在外的群体纳入进来,而后结构主义的课程史则从根本上反对围绕各种主体或行动者展开叙述,认为这是“意识哲学”在历史书写中的流毒。研究开始尝试将“主体”去中心化,反思预先设定行动者的优先地位给历史叙述造成的局限。正是所谓的“理性思维”制造了“人的类别”、制造了“区隔和分化”,后结构主义的历史研究要将这种思维规则本身置入历史语境中审视,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看待人、这样思考问题。用波普科维茨的话说,主体的“去中心化”就是尝试不再把行动者和能动性作为历史解释的中心,把关注点放在“生产了统治与服从关系的话语空间”上。它关注的不是黑人,而是“黑人民族性”(Blackness)的建构;不是妇女,而是“性别”的建构;不是孩子们,而是“童年”的建构[18]。
总之,反思主体或者说解构“主体”,并非抛弃人的能动性,而是以新的方式观察人们所受到的制约,并寻找突破这些制约的可能。它也不是要消弭“主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突破“类别和归属”的“解域之线”,让我们由此“逃逸”[29]。
三、结语
本文将美国课程史研究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置于美国课程理论、教育史学乃至史学研究的整体学术络脉中进行把握,从研究的内容、历史书写的方式以及对“主体”的处理等三个维度分析了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即从着重书写思想史转向书写社会史,而后又转向“新文化史”;从依循“重构史学”的路径,转向“建构史学”再转向“解构史学”;历史研究关注的“主体”从单一转向多元,之后又转而将“主体”本身也作为历史的建构物进行反思。每个维度上都存在一条贯串各个时期的发展线索(见表1)。
表1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多维演变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其一,本文依据美国课程史学发展的整体态势作出“前概念重建”、“概念重建”和“后概念重建”的划分,这并不是严格的分期。三者在时间上有重叠,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因为研究范式不可能于一夜之间更新。“旧的”研究方式有很强的延续性,甚至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仍有人坚持进行“前概念重建”式的课程史研究③。
其二,一些学术生涯较长、又对新的研究取向持开放态度的课程史学者的多部作品可能分属不同时期。比如“前概念重建期”的代表人物克利巴德后来也开展了一些具有明显课程社会史色彩的案例研究,“概念重建期”的代表富兰克林后来在波普科维茨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文化史”范式。
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课程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史学理论和课程理论的滋养,同时又从自身丰硕的学术成果中汲取力量,推动着课程领域的整体进步。假若课程学者们没有将“具有显著程序主义特征”的课程开发范式置入历史中审视其局限性,概念重建不会如此成功地开创理论新局面;同样,如果没有历史的视野,后概念重建时期的课程研究也无法摆脱对“再生产”和“抵制”等概念的依赖,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用知识创新不断突破“课程领域自身的概念枯竭”的困境。
注释:
①所谓的课程史研究的“进步取向”,把课程史领域产生之前出版的一些涉及到课程史内容的一般教育史著作,或者包含一定历史考察的课程理论研究当做课程史研究,这是值得商榷的。正如克利巴德所说,当他还是一名研究生时(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并没有课程史研究这样一个学术领域,只是在一般的教育史研究中包含了一些“依后世观点可被看成是课程史的要素”。将“修正主义”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和斯普林等人的研究归入课程史领域,并将它们作为修正主义课程史学的代表,显然有失准确。
②问题包括:经验主义能保证历史成为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吗?所谓历史“证据”的特征是什么,它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历史学家本人、他所使用的社会理论以及他所建构的解释框架在历史理解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历史解释的叙述形式究竟有多重要?
③如Hlebowitsh于2005年发表在《课程探究》(Curriculum Inquiry)上的Generational ideas in curriculum: A historical triangulation一文。
参考文献:
[1]何珊云.课程史研究的经典范式与学术意义——试析《1893~1958年的美国课程斗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5):164-171.
[2]陈华.西方课程史的研究路径及内涵探析[J].全球教育展望,2012(4):10-15.
[3]杨智颖.课程史研究观点与分析取径探析:以Kliebard和Goodson为例[M].高雄: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2008:18-34.
[4] 叶波. 20世纪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取向[J].全球教育展望,2012(9):22-25.
[5] Kridel, C.& Newman, V. A random harvest: A multiplicity ofstudies in American curriculum history research[M]. Mahwah, 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3: 637-650.
[6] Franklin, B.M. Curriculum History: Its Nature and Boundaries[J].Curriculum Inquiry, 1977,7(1): 67-79.
[7] Tanner, D.& Tanner, L. 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ory intopractice[M]. New York: Macmillan, 1975.
[8] Tanner, L. N. Curriculum History as Usable Knowledge[J].CurriculumInquiry, 1982, 12(4): 405-411.
[9] 王文智.走向“后概念重建”的课程研究——以后结构女性主义课程史为例[J].全球教育展望,2014(10):21-29.
[10] Bellack, A. A. History of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ractice[J].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9, 39(3): 283-293.
[11] Kliebard, H. M. Curricular objectives and evaluation: areassessment[J]. The High School Journal, 1968, 51(6): 241-247.
[12] Kliebard, H. M. The Tyler Rationale[J]. The School Review, 1970, 78(2): 259-272.
[13] Goodson, I. School subjects and curriculum change: studies incurriculum history[M]. Washington, D.C.: Falmer Press, 1983.
[14] Franklin, B. M. Building the American community : the schoolcurriculum and the search for social control[M]. London ; Philadelphia: FalmerPress, 1986.
[15] Popkewitz, T. S. Curriculum history, schooling and the history ofthe present[J]. History of Education, 2011, 40(1): 1-19.
[16] Tanner, D.& Tanner, L. N. History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M].New York: Macmillan, 1990: 8.
[17] 陈磊.超越新文化史范式?——读《后社会史初探》[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2(03):105-110.
[18]王文智.语言学转向:课程史研究的新取向[J].全球教育展望,2013(12):32-40.
[19] Popkewitz, T. S., Franklin, B. M.& Pereyra, M. A. Culturalhistory and education: critical essays on knowledge and schooling[M]. New York/London:Routledge Falmer, 2001:10.
[20]周兵.“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J].史学月刊,2006(4):12-17.
[21] Munslow, A. Deconstructing history[M].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2006.
[22] 邓京力.重构,建构与解构之间——从文学形式论史学类型与史学性质[J].史学理论研究,2012(1):41-50.
[23] 丹尼尔·坦纳,劳雷尔·坦纳.学校课程史[M].崔允漷,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24] 罗伯特•伯克霍福.超越伟大故事:作为话语和文本的历史[M].邢立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5] Kliebard, H. M. 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1893-1958[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ix.
[26] Hendry, P. M. Engendering curriculum history[M]. New York:Routledge, 2011: 4-15.
[27] 韩震.本质范畴的重建及反思的现代性[J].哲学研究,2008(12):54-57.
[28] Baker, B. Why Curriculum History is Not the Same as the History ofEducation: Post-Reconceptualist Approaches to Rethinking Education, Power, andthe Child主题演讲,2012年12月3日于浙江大学。
[29]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9-11.






